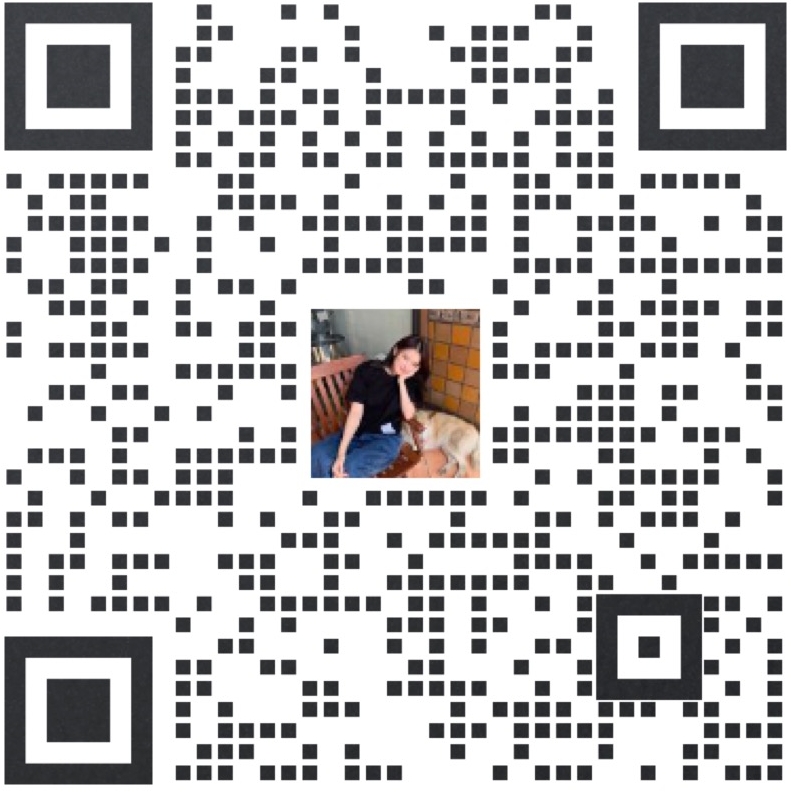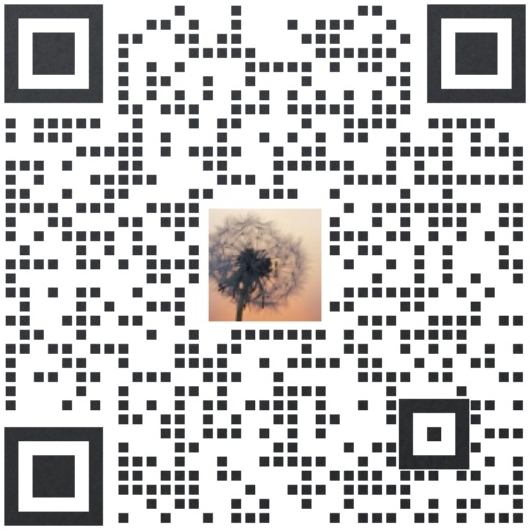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報記者 胡瑉琦
●張笑宇關(guan) 心的不是技術發展本身的脈絡,而是一些影響人類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背後發揮著隱秘作用的技術力量。
●胡翌霖認為(wei) ,如今技術迭代的速度早已不是以數百年為(wei) 單位了,隨著人類的壽命在增長,人類代際更迭的速度在放緩。這就導致原先可能是十代人前赴後繼去適應一項新技術,今天是一代人就要去適應十項新技術。
時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肆虐,這種病毒所到之處總能讓其所在社會(hui) 運轉體(ti) 係的問題暴露無遺。這也是為(wei) 什麽(me) 今天醫療技術如此發達,我們(men) 仍不能很快戰勝疫情的原因。
早在去年疫情暴發期間,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笑宇就提出了一個(ge) 疑問:疫情防控,在多大程度上是個(ge) 技術問題?他認為(wei) ,醫療技術的進步並不意味著公共疾控政策的進步。
而在那之前,他正在進行一項相關(guan) 的學術研究,把技術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角色,放到人類文明史的敘事中,將其和政治、經濟、軍(jun) 事、宗教等角色深度融合到一起,探討它們(men) 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如何影響世界的發展。
最近,張笑宇把研究內(nei) 容匯集到了《技術與(yu) 文明》這本書(shu) 中,而他所提供的研究視角,也引發了人們(men) 對於(yu) 技術史闡述方式,以及大眾(zhong) 究竟能夠從(cong) 技術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理解中得到什麽(me) 的思考。
換一種視角講述技術史
弩,如何扣動了中國大一統的扳機?新教改革與(yu) 自由思想的傳(chuan) 播當然關(guan) 乎我們(men) 現代社會(hui) 的誕生,技術在其中又怎樣決(jue) 定著關(guan) 聯者的“生死時速”?現代資產(chan) 階級革命牽涉到國家政體(ti) 與(yu) 結構的根本變化,但這又是在何種意義(yi) 上由關(guan) 鍵技術進步引發的鏈式反應?20世紀最重要的兩(liang) 大思潮——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自由主義(yi) 又是在怎樣的技術變革中突然爆發出來的?……
在《技術與(yu) 文明》中,張笑宇從(cong) 政治哲學研究的視野中選擇了14個(ge) 曆史關(guan) 鍵時刻,觀察和分析了技術如何改變人類命運。他說,他關(guan) 心的不是技術發展本身的脈絡,而是一些影響人類曆史走向的最重大事件背後發揮著隱秘作用的技術力量。
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意識到,社會(hui) 製度的先進與(yu) 落後,與(yu) 技術的先進與(yu) 落後之間存在複雜的內(nei) 在關(guan) 聯。技術不僅(jin) 可以快速、大規模、基礎性地改變人類物質世界的底層結構,也可以對上層文明產(chan) 生根本性影響。
這樣一種跨界研究的思路,也得到了清華大學科學史係副教授胡翌霖的認同。
他說,技術史在某種意義(yi) 上“超前”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事件曆史”,各種曆史事件的發生都需要某個(ge) “舞台”,而技術則決(jue) 定了這些“舞台”是如何搭建起來的。
“傳(chuan) 統的曆史學家並不會(hui) 在傳(chuan) 統曆史敘事中忽略諸如火藥、鐵路、堅船利炮、原子彈等關(guan) 鍵技術。不過,在那些敘事中,它們(men) 往往還是作為(wei) 主角和重要事件的附屬物被關(guan) 注的。”
因此,他認為(wei) ,技術通常被當作被動的因素看待,史學家較少注意它們(men) 積極的塑造性的麵相。比如說我們(men) 可能說秦國窮兵黷武、重視戰爭(zheng) ,所以積極製備各種武器;但很少討論因為(wei) 特定武器的革新,反過來促進了秦國的軍(jun) 事製度和動員機製的發展。
“但事實上,‘技術史’研究本來就應該是多重視角的,比如考察各種事件所伴隨的器具和裝備、各種事件所立足的基礎和背景、在幕後驅動各種事件的技術邏輯,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針對某一種特定技術,可以同時有多個(ge) 視角。比如說戰國時期的‘弩機’技術,它既是很顯著的發明,也是戰爭(zheng) 的工具和背景,也提供了軍(jun) 事和政治製度的底層邏輯。”
胡翌霖告訴《中國科學報》,從(cong) 西方的技術史學科的發展來看,多視角相互融合的研究由來已久。他提到,“技術與(yu) 文明”這個(ge) 書(shu) 名至少在80多年前就有了,技術史的開山祖師之一、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出版的《技術與(yu) 文明》一書(shu) 就是不朽的經典。美國的技術史學會(hui) 在1950年代建立,從(cong) 學會(hui) 建立之初,很多重要的技術史學者就有經濟學或經濟史的背景,到七八十年代有更多人擁有政治學和社會(hui) 學的背景,以及哲學和神學的背景。而法國的技術史學科也是從(cong) 1950年代發展起來的,法國的特色是有更多人類學和哲學的背景。
“可以說技術史這種‘融合’的視野是國際上技術史學科的常態。隻是在中國,技術史的學科是相對孤立的,很多學者都是工程學或中國史的背景,經常是與(yu) 海外漢學家的交流更密切,而同國外技術史家的交流較少。因此,這類的研究視角在國內(nei) 看起來不多見,而這一點恰恰證明了國內(nei) 的技術史學科的發展還比較落後。”
困在鐵籠裏的技術
所有人都同意,我們(men) 今天已經進入一個(ge) 技術型社會(hui) 。如果在認知“技術”的時候,缺乏這種融合的視野或者曆史觀,會(hui) 發生什麽(me) ?
“我們(men) 注意到,曆史上技術的革新會(hui) 對人類文明的其它領域產(chan) 生推動,但在古代,這個(ge) 推動的進程往往是非常慢的。在數百年內(nei) ,有好幾代人窮其一生慢慢適應新事物,並逐漸施加改變——既需要一點一點改良技術,也需要一點一點改變政治製度、經濟模式、倫(lun) 理觀念等領域,來與(yu) 新技術相互磨合。”
但胡翌霖表示,如今技術迭代的速度早已不是以數百年為(wei) 單位了,隨著人類的壽命在增長,人類代際更迭的速度在放緩。這就導致原先可能是十代人前赴後繼去適應一項新技術,今天是一代人就要去適應十項新技術。
“盡管人類的政治學、倫(lun) 理學等領域的智慧也在積累,但發展的速度遠遠不如技術革新的速度。這種局麵注定會(hui) 導致人類在技術麵前越來越應接不暇,政治體(ti) 製和社會(hui) 結構隻能不斷接受新技術的衝(chong) 擊,而越來越難以主動發起回應。當我們(men) 主流的技術史觀仍然把技術看作被動和附屬的一方時,實際情況是人類社會(hui) 將淪為(wei) 技術的附庸。”
張笑宇指出,現今大多數人的思維模式是:技術背後的東(dong) 西與(yu) 我無關(guan) ,那是專(zhuan) 家、企業(ye) 或者專(zhuan) 業(ye) 組織的事。
“蘇格蘭(lan) 啟蒙運動年代,有一個(ge) 著名的組織叫月光社,瓦特、達爾文、富蘭(lan) 克林、托馬斯·傑弗遜的老師都是月光社的成員。當時,在啟蒙時代的‘桌子’上,這邊坐有人文學者,那邊坐有社會(hui) 科學學者,旁邊還坐著政治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和商人。這群人共同去探索自然的奧秘,發現技術力量去改造社會(hui) ,在當時是一個(ge) 不言而喻的常識。但這種傳(chuan) 統到了20世紀卻逐漸消失了。”
他解釋,隨著科學研究的進步,專(zhuan) 業(ye) 分工越來越細致,專(zhuan) 家、專(zhuan) 業(ye) 組織就被專(zhuan) 業(ye) 化的“鐵籠”所規訓了,他們(men) 的身邊不再有“圓桌”。
“分工造成的割裂對現代文明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鐵籠子裏的專(zhuan) 家很難明白自身行事的尺度。”他舉(ju) 例,比如,人工智能領域的專(zhuan) 業(ye) 學者可以采取大數據算法來判斷什麽(me) 樣的人的麵相更具備犯罪傾(qing) 向;但是,如果他不具備相關(guan) 的曆史與(yu) 社會(hui) 學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他就不會(hui) 清楚這種顱相學研究當年是如何為(wei) 納粹的種族主義(yi) 辯護的。基因學領域的學者已經可以在孕婦身上直接實驗針對胎兒(er) 的基因編輯;但是,如果他不具備相關(guan) 的人文倫(lun) 理素養(yang) ,他就無法估量這種技術所產(chan) 生的社會(hui) 後果,並最終受到法律的製裁。
“曆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人類生活的秩序是由各種各樣的組織、專(zhuan) 家群體(ti) 提供的,比如教會(hui) 、商人同盟、宗族、企業(ye) 或者私人機構。現如今,大量技術公司早已喪(sang) 失了曆史記憶,沒有自覺意識到在提供技術的同時,應該為(wei) 社會(hui) 創造一個(ge) 怎樣的健康秩序,而隻是天天思考應該如何賺更多錢,讓公司的財務報表更好看。”也正因如此,張笑宇認為(wei) 更要從(cong) 本源的角度來探索文明秩序的生成曆史,然後把這些曆史經驗都複活起來。
做“跨域”的人
理解和認知技術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融合關(guan) 係,會(hui) 對大眾(zhong) 的曆史觀產(chan) 生怎樣的積極影響?
在胡翌霖看來,普通人的技術史觀,首先是可以看到普通人是有改變曆史的力量的。在傳(chuan) 統的以英雄人物或王侯將相為(wei) 主角的曆史敘事中,很少看見普通人的作用,但是在技術史的視野下,更有可能看到普通人的力量。
“對於(yu) 英雄也好,專(zhuan) 家也好,普通人也好,每一個(ge) 人的每一次選擇,都是有意義(yi) 的,而人類並不是機器,我們(men) 有情緒、有理想、有信念、有審美,我們(men) 的選擇總是基於(yu) 複雜多元的理由。當我們(men) 了解到我們(men) 的選擇有曆史意義(yi) 的時候,我們(men) 或許至少會(hui) 對自己的選擇多一層審視。”
其次,他認為(wei) ,普通人了解技術史之後,更有可能摒棄傳(chuan) 統的“技術中性論”——技術“僅(jin) 僅(jin) 是技術”,而與(yu) 政治、倫(lun) 理、社會(hui) 等人文領域或價(jia) 值尺度毫無關(guan) 係。人們(men) 一般以為(wei) 武器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善惡好壞總是取決(jue) 於(yu) 使用技術的人。這一觀念過於(yu) 簡單化。
比如弩機促進了大一統,並不單純是因為(wei) 弩機作為(wei) 武器更加強大從(cong) 而有利於(yu) 征服,而是因為(wei) 弩機的標準化生產(chan) 和規模化配備的特點,和特定的政治製度互相促進,推動了大一統的進程。可見武器的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體(ti) 現在它作為(wei) 殺人工具是否強有力,還體(ti) 現在它對政治和社會(hui) 等各個(ge) 維度的影響。
胡翌霖表示,技術總會(hui) 過時,但這種看待技術的視角並不過時,今天我們(men) 在討論芯片技術、5G技術、航天技術等問題的時候,也離不開政治、經濟等維度。
“作為(wei) 普通人,也許不那麽(me) 關(guan) 心家國命運,而是更關(guan) 心自己和家人。在這個(ge) 層麵上,技術史也能提供許多啟發。技術史和技術哲學幫助我們(men) 認識技術與(yu) 人性互相塑造的關(guan) 係。”
此外,進入技術型社會(hui) ,理解技術史也可以幫助人們(men) 洞察,究竟要成為(wei) 什麽(me) 樣的人才可能影響曆史,至少不被曆史所淘汰。
對於(yu) 這個(ge) 問題,張笑宇給出的答案是,“跨域”的人,也就是學會(hui) 連接技術和人。而“跨域”能力的核心是認識技術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
“你並不是要把一項技術賣給什麽(me) 人,而是要發現,某項技術能夠為(wei) 哪一領域帶來價(jia) 值。為(wei) 此,既要真正了解這項技術能夠實現什麽(me) 、它的優(you) 缺點和發展進程大致是怎樣的,又要了解它所施展的領域、它真正的需求在哪裏、市場規模是怎樣的、能夠取得多大的替代效應。”
因此,張笑宇的建議是,如果你是技術型人才,不妨借鑒一下社會(hui) 科學的視角;如果你更擅長人文社科領域,不妨試著關(guan) 心一下技術上的“硬變量”。
《中國科學報》 (2021-06-17 第5版 文化周刊)關注【深圳科普】微信公眾號,在對話框:
回複【最新活動】,了解近期科普活動
回複【科普行】,了解最新深圳科普行活動
回複【研學營】,了解最新科普研學營
回複【科普課堂】,了解最新科普課堂
回複【科普書籍】,了解最新科普書籍
回複【團體定製】,了解最新團體定製活動
回複【科普基地】,了解深圳科普基地詳情
回複【觀鳥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學習觀鳥相關科普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
回複【博物學院】,了解更多博物學院活動詳情

 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