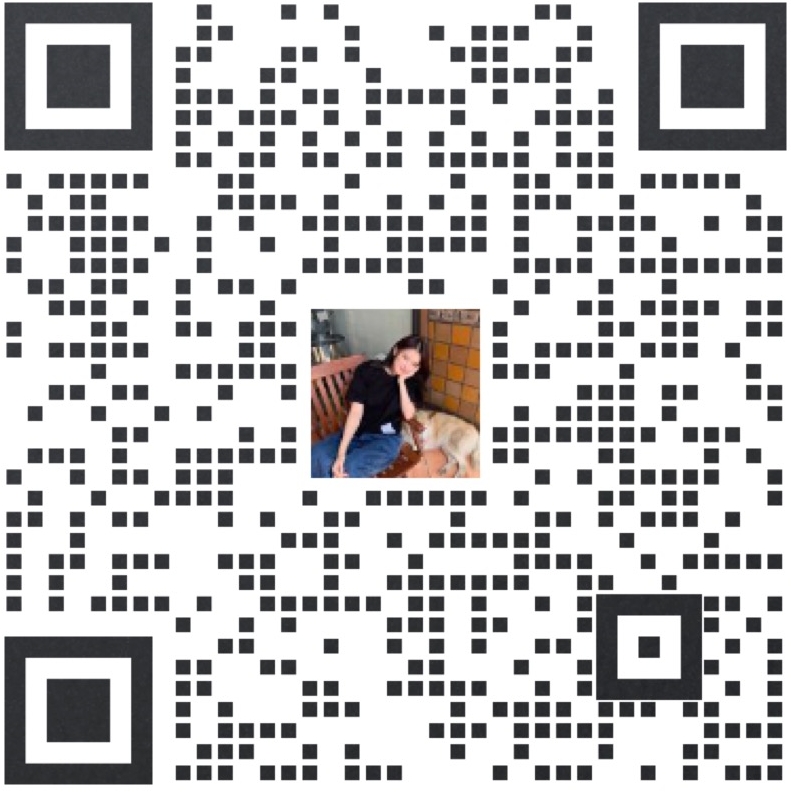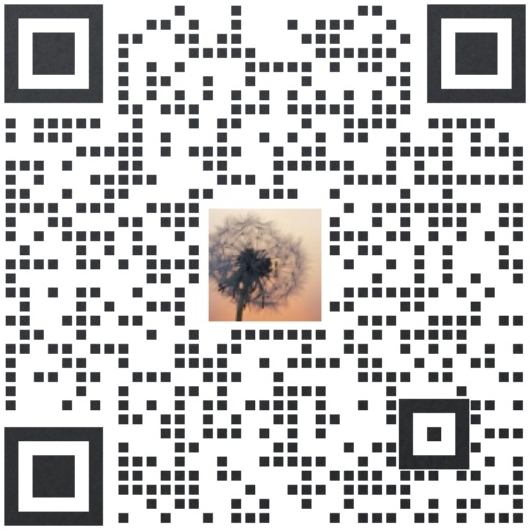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係我們(men)
© The Guardian
利維坦按:
當一種解釋不適用於(yu) 當下情況,要麽(me) 是這套解釋錯了,要麽(me) 是這套解釋不完備,也就是說有其他未知的原因促成這般局麵。正因如此,很多科學家們(men) 一直在尋找“大一統理論”,就像愛因斯坦在晚年所做的那樣。物理學如此,化學如此,生物學亦如此。達爾文所提出的進化論自麵世以來就一直受到質疑,有人說它錯了,有人說它不完備。其背後自然是希望找到一套能夠盡可能解釋所有生物學現象的理論——所以,如果它錯了,究竟錯在哪了?
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關(guan) 於(yu) 地球上生命進化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例如眼睛是如何形成的,科學家們(men) 仍然一無所知。關(guan) 於(yu) 人類是如何擁有這樣一對極其複雜的器官,通常的解釋都是自然選擇理論。
你或許還記得學校生物課上教的東(dong) 西。如果一個(ge) 視力差的物種碰巧因為(wei) 隨機突變而繁衍出視力稍好一些的後代,那麽(me) 這個(ge) 進步會(hui) 給它們(men) 更多的生存機會(hui) 。存活時間越長,它們(men) 繁衍後代的幾率就越大,也越有可能將優(you) 勢基因遺傳(chuan) 給下一代。
同樣地,再下一代的視力也有可能更好一些,繁殖幾率也更大。如此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在漫長的時間裏,這些微小的優(you) 勢基因不斷疊加,最終,幾億(yi) 年後,這個(ge) 物種就會(hui) 變得和人、貓或者貓頭鷹一樣視力敏銳。
這就是各大教科書(shu) 和科普暢銷書(shu) 中常見的進化基本原理。但是,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質疑,這種說法完全是謬誤和誤導。
首先,這一說法忽略了進化的起源,認為(wei) 感光細胞,晶狀體(ti) 和虹膜是天然存在的,而沒有解釋它們(men) 從(cong) 何而來。同時(傳(chuan) 統進化理論)也沒有解釋清楚這些脆弱且不堪一擊的部分是如何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ge) 單一器官的。並且,不光是眼睛,其他傳(chuan) 統理論也遭到質疑。
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生物學家阿明·莫切克(Armin Moczek)表示,“第一隻眼睛,第一隻翅膀,第一個(ge) 胎盤,都是怎麽(me) 形成的?解釋這些問題是進化生物學的基本動力,但目前我們(men) 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傳(chuan) 統理論認為(wei) ,進化是通過每一次意外的進步逐步改變,這種解釋已經不再成立。”
© Medium
有一些核心的進化原則沒有遭到科學家嚴(yan) 厲質疑。比如,他們(men) 一致認為(wei) ,自然選擇,突變和隨機因素起到了作用。但這些過程到底如何相互作用,是否還有其他的作用因素?這些問題成為(wei) 了討論的焦點。耶魯大學生物學家甘特·瓦格納(Günter Wagner)告訴我說, “如果我們(men) 不能用現有工具解釋這些問題,我們(men) 就必須另尋方法。”
2014年,八位科學家就這點在權威雜誌《自然》(Natur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並提問“我們(men) 需要重新思考進化論嗎?”他們(men) 的回答是:“是的,而且迫切需要!”
這八位科學家都來自前沿科學領域,比如,生物如何改變所在環境從(cong) 而減少自然選擇的普遍壓力(類似於(yu) 海狸建水壩),還有,人體(ti) DNA的化學修飾可以遺傳(chuan) 給下一代這類最新研究。他們(men) 呼籲革新進化理論,從(cong) 而為(wei) 其他前沿科學領域的研究提供支持。他們(men) 稱這種新理論框架為(wei) 擴展進化綜論(the 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EES)——一個(ge) 平平無奇的名字,但對許多同行來說,他們(men) 的提議極具煽動性。
(www.nature.com/articles/514161a)
© Utah Public Radio
2015年,英國皇家學會(hui) 同意舉(ju) 辦“進化論新風向(New Trends in Evolution)”會(hui) 議,文章的八位作者和一批傑出的科學家將在會(hui) 上發言。一位組織者稱,此次會(hui) 議的目的是討論“新的解釋,新的問題,以及一個(ge) 全新的生物學因果結構”。
但當會(hui) 議宣布後,英國皇家學會(hui) 的23位成員向時任主席、諾貝爾獎得主保羅·納斯爵士(Sir Paul Nurse)遞交了聯名抗議書(shu) 。據一位簽名者所說,“學會(hui) 召開會(hui) 議的舉(ju) 動讓我們(men) 覺得很丟(diu) 臉,因為(wei) 這會(hui) 讓公眾(zhong) 認為(wei) 這些(新)思想是學術主流。” 納斯對於(yu) 這樣的反應表示驚訝,他說:“他們(men) 認為(wei) 我太過相信新觀點了。但討論問題並沒有壞處。”
會(hui) 議邀請了傳(chuan) 統的進化理論家,但鮮有人出席。2008年進化生物學最高榮譽達爾文-華萊士獎章得主尼克·巴頓(Nick Barton)告訴我,他“決(jue) 定不去,因為(wei) 這會(hui) 給這項奇怪的事業(ye) 造勢”。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頗具影響力的生物學家布賴恩·查爾斯沃思(Brian Charlesworth)和黛博拉·查爾斯沃思(Deborah Charlesworth)告訴我說,他們(men) 之所以沒有參加,是因為(wei) 覺得這個(ge) 理論的前提“令人惱火”。
進化理論家傑裏·科因(Jerry Coyne)後來寫(xie) 到,提出EES的科學家們(men) 實際上借“革命者”之名推進自己的事業(ye) 。一份2017年的論文甚至指出,EES背後的一些理論家實際上體(ti) 現了科學界“愈演愈烈的後真相趨勢”。一位科學家表示,針對EES科學家的人身攻擊和隱射“不堪入目”,“令人震驚”。但即便如此,他也對EES持懷疑態度。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041-017-0787-6)
為(wei) 何會(hui) 出現如此強烈的反駁?一方麵,這是一場關(guan) 乎進化論命運的思想戰爭(zheng) ,現代社會(hui) 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賴於(yu) 這一偉(wei) 大理論。另一方麵,這也是一場關(guan) 乎專(zhuan) 業(ye) 認可和地位的鬥爭(zheng) ——誰來決(jue) 定什麽(me) 是這個(ge) 學科的核心,什麽(me) 是次要的。
馬裏蘭(lan) 州IBBR研究院的進化理論家阿林·斯托爾茨福斯(Arlin Stoltzfus)表示:“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誰將掌握書(shu) 寫(xie) 生物學宏大敘事的主導權。”另外還有一個(ge) 更深層次的問題:當前這個(ge) 生物學的偉(wei) 大理論敘事是否是一場童話,最終是否需要放棄?
﹡﹡﹡
在當前有關(guan) 進化的爭(zheng) 論背後藏著一個(ge) 破碎的夢。20世紀早期,許多生物學家渴望找到一種統一的理論,能夠讓生物學和物理學以及化學一樣,成為(wei) 把世界分解為(wei) 一套基本規則的樸素且機械的科學學科。
他們(men) 擔心,如果沒有統一的理論,生物學仍將被切割為(wei) 從(cong) 動物學到生物化學等諸多難以解決(jue) 的子領域,回答這些領域中的任何問題都可能需要許多彼此不和的專(zhuan) 家各抒己見,最終導致爭(zheng) 論不休。
© Phys.org
從(cong) 今天觀點來看,我們(men) 很容易得出,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種簡單巧妙的理論,解釋了自然選擇這一種因素如何塑造了整個(ge) 地球上生命的發展——將扮演偉(wei) 大的統一者的角色。但是,在20世紀初,也就是《物種起源》出版40年,達爾文去世20年後,他的思想開始衰落。當時出現了題為(wei) 《達爾文主義(yi) 的窮途末路》(The Death-bed of Darwinism)等科學作品。
科學家們(men) 並非失去了對進化論的興(xing) 趣,隻是許多人認為(wei) 達爾文對進化論的敘述不盡人意。其中一個(ge) 主要問題是,它缺少對遺傳(chuan) 的解釋。達爾文觀察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物似乎會(hui) 發生變化以更好地適應環境。但他不理解這些微小的變化是如何代代相傳(chuan) 的。
達爾文曾寫(xie) 道:“自然從(cong) 不飛躍。”突變論者對此表示異議。
20世紀初,對天主教會(hui) 修士和現代遺傳(chuan) 學之父格雷戈爾·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發現的重新研究給上述問題帶來了答案。致力於(yu) 遺傳(chuan) 學新領域的科學家發現了控製遺傳(chuan) 奧秘的規律。但這不是對達爾文理論的驗證,反而使其複雜化了。
繁殖似乎以令人驚訝的方式重組了基因,這些神秘的遺傳(chuan) 物質決(jue) 定了我們(men) 最終看到的生理特征。舉(ju) 個(ge) 例子,外祖父的紅頭發沒有遺傳(chuan) 給兒(er) 子,反而遺傳(chuan) 給了孫女。當微小的變異甚至不能連續出現在每一代人身上時,自然選擇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
© Nautilus Magazine
對於(yu) 達爾文主義(yi) 者來說,更大的威脅是20世紀10年代出現的“突變論者”。這一派遺傳(chuan) 學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托馬斯·亨特·摩爾根(Thomas Hunt Morgan),他證明,在培育數百萬(wan) 隻果蠅的過程中,將其食物用放射性鐳進行標記,就可以讓果蠅產(chan) 生突變性狀,比如出現新的眼睛顏色或長出額外的肢體(ti) 。這些變化並非達爾文理論所提出的隨機的、微小的變化,而是突然的、巨大的變化。
事實證明,這些突變是可遺傳(chuan) 的。突變論者認為(wei) 他們(men) 發現了生命真正的創造力。無疑,自然選擇幫助排除了不合適的變化,但它隻是在華麗(li) 的突變詩歌上做著單調的編輯。達爾文曾寫(xie) 道:“自然從(cong) 不飛躍。”突變論者對此表示異議。
托馬斯·亨特·摩爾根(1866-1945),美國遺傳(chuan) 學家、現代遺傳(chuan) 學之父。他在對黑腹果蠅遺傳(chuan) 突變的研究中,首次確認了染色體(ti) 是基因的載體(ti) ,還找出了多個(ge) 突變基因在染色體(ti) 上的分布位置,因此獲1933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此外,他還發現了遺傳(chuan) 連鎖定律。© Linda Hall Library
關(guan) 於(yu) 進化論的爭(zheng) 論有神學上的分歧。這關(guan) 係到支配萬(wan) 物的力量。尤其對於(yu) 達爾文主義(yi) 者來說,他們(men) 的理論要麽(me) 被全部保留,要麽(me) 被全部推翻。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寫(xie) 到,如果有除了自然選擇之外的另一種力量也能解釋生物之間的差異,那麽(me) 他的整個(ge) 生命理論將“徹底崩潰”。
如果突變論者是正確的,科學家就必須深入研究突變的邏輯,而不是相信單一的力量可以控製所有生物變化。他們(men) 需要研究突變對於(yu) 腿部和肺部的作用是否不同?青蛙的突變與(yu) 貓頭鷹或者大象的突變是否有差異?
1920年,哲學家約瑟夫·亨利·伍格(Joseph Henry Woodger)寫(xie) 到,生物學遭遇了“分裂和分歧”,而這是“化學等統一的學科不會(hui) 見到的”。他注意到,有分歧的群體(ti) 之間經常出現爭(zheng) 執,並且愈演愈烈。生命科學將變得越來越支離破碎,尋找共同語言的可能性趨向於(yu) 零,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
就在達爾文主義(yi) 似乎要被塵封之時,統計學家和動物育種學家這一對奇妙的組合出現了,為(wei) 它重新注入生機。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不同地方各自工作,卻保持著偶爾聯係的英國科學統計之父羅納德·費希爾(Ronald Fisher)和美國遺傳(chuan) 學家休沃爾·賴特(Sewall Wright)等思想家提出了一個(ge) 修正的進化理論。
該理論闡釋了自達爾文去世以來的科學進步,但仍然試圖用一些簡單的規則解釋所有生命的奧秘。1942年,英國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給這一理論命名為(wei) “現代綜論”(the modern synthesis)。80年過去了,它仍然是進化生物學的基本框架,每年出現在數百萬(wan) 小學生和大學生的課本之中。研究現代綜論的生物學家被認為(wei) 是“主流”,否則就是“非主流”的。
英國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在學會(hui) 上發表演講。© Felix Man/Getty Images
“現代綜論”其實並非兩(liang) 個(ge) 領域的綜合,而是一個(ge) 領域對另一個(ge) 領域的驗證。通過建立動物種群的統計模型以解釋基因和突變的規律,現代綜論學家表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自然選擇仍然像達爾文預測的那樣發揮作用,並仍是起主導作用。但如果把時間拉到很長,突變實際上很少見,影響甚微,而遺傳(chuan) 規律也不會(hui) 影響自然選擇的整體(ti) 作用。慢慢地,優(you) 勢基因會(hui) 保留下來,其他沒有優(you) 勢的基因則會(hui) 消失。
現代綜論的支持者並未鑽牛角尖於(yu) 龐雜世界中單個(ge) 生物及其所處的特定環境,相反,他們(men) 從(cong) 群體(ti) 遺傳(chuan) 學的高度進行觀察。對他們(men) 而言,生命說到底不過是一連串基因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生死存亡的故事。
現代綜論出現得恰逢其時。除了科學解釋效力外,還有兩(liang) 個(ge) 更偏曆史學的、或者是社會(hui) 學的原因。首先,綜論的數學嚴(yan) 謹性令人印象深刻,且在生物學中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曆史學家貝蒂·斯莫科維蒂斯(Betty Smocovitis)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嚴(yan) 謹性使得該領域更加接近於(yu) 類似物理學的“範例科學”。同時,在科學統一的啟蒙計劃風靡一時之際,它有望統一整個(ge) 生命科學。
1946年,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和喬(qiao) 治·蓋洛德·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創辦了進化研究協會(hui)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volution),該專(zhuan) 業(ye) 協會(hui) 擁有自己的期刊,辛普森認為(wei) 協會(hui) 將在“進化研究的共同基礎上”匯總生物學的各個(ge) 子領域。他後來認為(wei) ,一切皆有可能,因為(wei) “我們(men) 似乎終於(yu) 擁有了一種統一的理論……能夠應對生命研究曆史上所有經典問題,並且能夠為(wei) 每一個(ge) 問題提供因果關(guan) 係的解決(jue) 方案”。
(www.jstor.org/stable/4331311)
(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739-019-09569-2)
此時,生物學已經上升為(wei) 一門主流科學。相關(guan) 院係在大學裏紛紛成立,資金源源不斷流入,數千名新獲得認證的科學家得到激動人心的發現。1944年,加拿大裔美國籍生物學家奧斯瓦爾德·艾弗裏(Oswald Avery)和同事證明了DNA是基因和遺傳(chuan) 的物理物質。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裏克(Francis Crick)通過大量研究羅莎琳·富蘭(lan) 克林(Rosalind Franklin)和美國化學家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的工作成果,繪製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圖。
1953年,詹姆斯·沃森(左)和弗朗西斯·克裏克在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DNA模型前。© Cavendish Laboratory
信息積累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yu) 沒有一個(ge) 科學家能夠完全消化,但現代綜論的穩定節奏貫穿始終。該理論指出,歸根到底,基因塑造了一切,且自然選擇會(hui) 審視生命的每一點優(you) 勢。無論是池塘中茂密生長的海藻,還是孔雀的交配儀(yi) 式,都可以被理解為(wei) 自然選擇在基因上作用的結果。生命世界似乎突然又變得簡單起來。
到了1959年,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舉(ju) 行了慶祝《物種起源》出版100周年的會(hui) 議,現代綜論家們(men) 春風得意,會(hui) 場座無虛席,全國各大報紙爭(zheng) 相報道(伊麗(li) 莎白女王也受到了邀請,但致歉說不能到場)。赫胥黎得意地表示,“這是開天辟地的頭一次。在公開場合坦率承認現實的所有方麵都有賴於(yu) 進化。”
然而很快,現代綜論就受到了其所幫助建立的各個(ge) 部門科學家的攻擊。
﹡﹡﹡
從(cong) 一開始,反對者就一直存在。
1959年,發育生物學家CH·沃丁頓(CH Waddington)發出哀歎,稱現代綜論導致有價(jia) 值的理論被邊緣化,它支持“極端的簡化,這容易導致我們(men) 對進化過程產(chan) 生錯誤的印象”。私下裏他抱怨稱,任何居於(yu) 新進化“黨(dang) 派線路”之外的人都被看作不支持現代綜論的人,都要遭到排斥。
隨後,一係列重大新發現對該理論的基礎提出質疑。這些發現始於(yu) 上世紀60年代末,由分子生物學家提出。質疑稱,現代綜論家們(men) 就好似通過望遠鏡觀察生命,研究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大量種群整體(ti) 的進化。而分子生物學家則是通過顯微鏡觀察生命,聚焦於(yu) 單個(ge) 分子。他們(men) 發現,自然選擇並不像人們(men) 認為(wei) 的那樣是主導一切的力量。
© Maria Nguyen/Quanta Magazine
他們(men) 發現我們(men) 細胞中的分子以及當中的基因序列是在以非常快的速度進行突變。這點出乎意料,但並非一定會(hui) 對主流進化論產(chan) 生威脅。
根據現代綜論,即使突變時常發生,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選擇依舊是變化的主要原因,保留有用突變,去除無用突變。但事實並非如此。基因不斷變化(也就是進化),但自然選擇並未發生作用。一些基因變化純粹是通過偶然保存下來,自然選擇在此期間似乎陷入“沉睡”。
進化生物學家為(wei) 此大為(wei) 震驚。1973年,大衛·愛登堡(David Attenborough)主持了一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紀錄片,其中包括了對一位著名現代綜論家狄奧多西·多布讚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采訪。後者顯然對一些科學家提出的“非達爾文進化論”感到心煩意亂(luan) 。
他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進化就變得沒有意義(yi) 了,也不會(hui) 有任何發展。這不光是專(zhuan) 家的抱怨。對於(yu) 每一個(ge) 尋找生存意義(yi) 的人來說,自然選擇進化是有意義(yi) 的。”
曾經,基督教徒批評達爾文理論讓生命變得沒有意義(yi) ,現在,達爾文理論者也向反對達爾文的科學家發出同樣的批評。
其他對進化論主流觀點的抨擊接踵而至。頗具影響力的古生物學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奈爾斯·埃爾德雷奇(Niles Eldredge)認為(wei) ,化石記錄表明,進化經常是在短時間內(nei) 集中爆發,不一定是緩慢且循序漸進的。
(www.jstor.org/stable/2400177)
其他生物學家發現現代綜論和他們(men) 的工作幾乎沒有關(guan) 聯。隨著對生命的研究越來越複雜,一個(ge) 基於(yu) 在不同環境中哪種基因會(hui) 被選擇的理論開始顯得無關(guan) 緊要。它無法幫助回答海洋中是如何出現生命的,或者像胎盤這樣的複雜器官是如何發育的問題。
© House Of Solutions
耶魯大學發育生物學家甘特·瓦格納(Günter Wagner)說,用現代綜論來解釋後者,就“好像用熱力學來解釋大腦是如何工作的”。(熱力學定律解釋了能量如何是傳(chuan) 遞的,它確實被用於(yu) 大腦研究中,不過要是想知道記憶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們(men) 為(wei) 何會(hui) 有情感體(ti) 驗,這一定律並無用武之地。)
正如人們(men) 擔心的那樣,生物學出現了分裂。1970年代,許多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從(cong) 生物係中剝離出來,成立了自己的院係和期刊。其他子領域的一些學科,比如古生物學和發育生物學,也逐漸分離出去。然而最大的領域,即主流進化生物學,仍然和以前一樣。
現代綜論的擁護者——他們(men) 在當時占據了大學生物係的主導地位——為(wei) 了避免破壞穩定,他們(men) 可能的處理方式是承認這些過程隻是偶爾會(hui) 發生(潛台詞:很少),且隻對一些專(zhuan) 家(潛台詞:不清楚具體(ti) 是哪些專(zhuan) 家)有意義(yi) ,但不會(hui) 從(cong) 根本上改變從(cong) 現代綜論傳(chuan) 承下來的對生物學的基本理解(潛台詞:不用擔心,我們(men) 不會(hui) 改的)。簡而言之,他們(men) 認為(wei) 新發現不過是一些奇聞趣事,並不予理會(hui) 。
進化理論家道格拉斯·福圖馬(Douglas Futuyma)在2017年一篇捍衛主流觀點的論文中寫(xie) 到,如今,現代綜論“在做了必要的修改後仍然是現代進化生物學的核心”。改良後的現代綜論允許突變和隨機概率的存在,但仍將進化視為(wei) 基因在大量種群中生存的故事。或許,與(yu) 該理論在50年代的輝煌時期相比,最大的變化是它最具野心的主張——隻要理解基因和自然選擇,我們(men) 就能理解地球上所有生命——已經被拋棄,或者說帶有警告和例外。
(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fs.2016.0145)
這種轉變發生得悄無聲息。該理論的一些思想仍然深深根植於(yu) 該領域,但它的失敗和分裂並未出現正式的反噬。在批評者看來,現代綜論的地位就如同背棄競選承諾的總統——它未能讓整個(ge) 聯盟滿意,盡管已經威望不再,但仍然穩居高堂,手握大權。
© Fact Retriever
布賴恩·查爾斯沃斯和黛博拉·查爾斯沃斯被許多人認為(wei) 是現代綜論傳(chuan) 統的大祭司。他們(men) 是傑出的思想家,寫(xie) 了大量關(guan) 於(yu) 新理論在進化生物學中地位的文章,並且認為(wei) 不需要做任何激進的修正。有人認為(wei) 他們(men) 過於(yu) 保守,但他們(men) 堅持說自己不過是小心謹慎,避免廢除一個(ge) 經過驗證的框架,反而支持缺乏證據的理論。他們(men) 感興(xing) 趣的是進化的基本真理,而不是解釋進化的每一種不同的結果。
布賴恩·查爾斯沃斯告訴我:“我們(men) 不是為(wei) 了解釋大象為(wei) 什麽(me) 有長鼻子,或者駱駝為(wei) 什麽(me) 有駝峰,如果這樣的解釋存在的話。”他說,相反,進化論應該是普遍適用的,應該專(zhuan) 注適用於(yu) 所有生命進化規律的少數因素。黛博拉說:“人們(men) 很容易糾結‘為(wei) 什麽(me) 你不能解釋某個(ge) 特定的係統是怎麽(me) 工作的’。但其實我們(men) 不需要知道。”這不是因為(wei) 這些例外情況不有趣,它們(men) 隻是沒那麽(me) 重要。
﹡﹡﹡
科學家凱文·拉蘭(lan) 德(Kevin Laland)是備受爭(zheng) 議的皇家學會(hui) 會(hui) 議的組織者,他認為(wei) 是時候讓那些被忽視的進化論子領域的支持者聯合起來了。拉蘭(lan) 德和其他EES支持者呼籲用一個(ge) 新方法思考進化——不是以尋找最簡單的或普遍的解釋為(wei) 出發點,而是以尋找最能解釋生物學主要問題的方法組合為(wei) 出發點。最終,他們(men) 希望自己所研究的子領域,比如可塑性、演化發育、表觀遺傳(chuan) 學以及文化演化等,不僅(jin) 得到承認,而且被納入生物學的經典。
這群人中也有一些煽動者。遺傳(chuan) 學家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宣稱自己是新拉馬克主義(yi) 者,這一名稱取自19世紀生物學家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他是在達爾文之前的遺傳(chuan) 思想的普及者,在科學界中飽受詬病。與(yu) 此同時,生理學家丹尼斯·諾布(Denis Noble)呼籲對傳(chuan) 統的進化理論進行一場“革命”。但是,作為(wei) 該運動中許多論文的主要作者,拉蘭(lan) 德堅持認為(wei) ,他們(men) 隻想擴展當前進化論的定義(yi) 。他們(men) 是改革者,不是革命者。
EES基於(yu) 一個(ge) 簡單的主張:在過去幾十年裏,我們(men) 發現了自然世界的非凡事物,它們(men) 應該在生物學的核心理論中有一席之地。在這些新領域中最令人著迷的一個(ge) 就是可塑性,它表明一些生物具有更快更徹底地適應環境的潛力,遠超人們(men) 曾經的想象。可塑性的相關(guan) 描述令人吃驚,讓人想起可能在漫畫書(shu) 和科幻電影中才會(hui) 出現的那種瘋狂變異。
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的動物學家艾米麗(li) ·斯坦登(Emily Standen)致力於(yu) 研究金恐龍,即塞內(nei) 加爾多鰭魚。這種魚不僅(jin) 有腮,還有原始的肺。她說,普通的金恐龍可以在水麵呼吸,但“更喜歡”生活在水下。而當斯坦登將在水下生活了幾周的小金恐龍拿到陸地上養(yang) 殖後,它們(men) 的身體(ti) 立馬開始發生變化。它們(men) 鰭上的骨頭變長變尖,關(guan) 節窩變得更寬,肌肉更大,能夠幫助它們(men) 在幹燥的陸地上拖行。它們(men) 的脖子更加柔軟,原始肺擴大,其他的器官也相應變化。它們(men) 完全變成了另一種樣子。
(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014.15778)
動物學家艾米麗(li) ·斯坦登發現,小金恐龍拿到陸地上養(yang) 殖後,其身體(ti) 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blickwinkel/Alamy/Central Florida Aquarium Society
斯坦登告訴我:“它們(men) 就好像是化石記錄中看到的,位於(yu) 海洋和陸地之間的過渡物種。”根據傳(chuan) 統的進化論,這種改變需要數百萬(wan) 年。但ESS的支持者阿明·莫切克(Armin Moczek)說,金恐龍“隻進化了一代就能適應在陸地上生活”。他聽起來頗為(wei) 這些魚兒(er) 們(men) 驕傲。
莫切克的研究領域是另一種可塑性極強的物種:蜣螂。考慮到未來的氣候變化,他和同事們(men) 測試了蜣螂對不同溫度的反應。在寒冷的天氣下,蜣螂難以起飛,但研究人員發現,它們(men) 會(hui) 長出更大的翅膀來適應寒冷環境。
(www.science.org/doi/full/10.1126/science.aaw2980)
© Armin Moczek
這些觀察結果的關(guan) 鍵之處在於(yu) ,此類突然的變化都來自同樣的潛在基因。這樣的發現挑戰了進化的傳(chuan) 統理解。蜣螂的基因並不是一代一代慢慢進化的,相反,在早期發展過程中,它具有以不同方式生長的潛力,使其能夠在不同的環境中生存。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大衛·芬尼格(David Pfennig)說:“我們(men) 相信這種現象在所有物種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他的研究對象是鋤足蟾,一種火柴盒玩具車大小的兩(liang) 棲動物。鋤足蟾是雜食動物,但如果隻喂它們(men) 肉,它們(men) 就會(hui) 長出更大的牙齒,更有力的下顎以及更堅韌、更複雜的腸道。突然之間,它們(men) 就變成了強大的肉食動物,以堅硬的甲殼類動物,甚至是其他蝌蚪為(wei) 食。
(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cannibalistic-tadpoles-and-matricidal-worms-point-powerful-new-helper-evolution)
可塑性並沒有否定通過選擇微小變化而循序進化的觀點,但提供了另一種自成邏輯的進化係統。對於(yu) 一些研究人員來說,這可能就是生物學中新奇事物出現的原因,比如第一隻眼睛,第一隻翅膀等。芬尼格說:“可塑性可能是激發生物體(ti) 形成一種新特征的基本形式。”
可塑性在發育生物學(Developmental biology)中被廣泛接受。它由開創性理論家瑪麗(li) ·簡·韋斯特·埃伯哈德(Mary Jane West-Eberhard)提出,是20世紀初一種核心的進化理論。然而,對於(yu) 許多其他領域的生物學家來說,這幾乎是未知的。大學新生不太可能接觸到它,科普作品中也很少見到。
生物學中類似的理論隨處可見。EES的其他新穎理論包括外基因遺傳(chuan) ,即表觀遺傳(chuan) 學。這種觀點認為(wei) ,父母經曆的一些事情,比如精神創傷(shang) 或疾病,會(hui) 導致小的化學分子附著在他們(men) 的DNA上,並遺傳(chuan) 到孩子身上。這一理論已經在一些動物身上被驗證,且可以在多代間實現遺傳(chuan) ,但當有人建議用它來解釋人類代際創傷(shang) 時,爭(zheng) 議便出現了。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parents-rsquo-trauma-leaves-biological-traces-in-children/)
表觀遺傳(chuan) 機製示意圖。© Novus Biologicals
還有的EES支持者研究文化等事物的遺傳(chuan) ,包括海豚群體(ti) 在發展過程中相互傳(chuan) 授新的捕獵技術,以及動物腸道或植物根部的有益微生物群——它們(men) 就像工具一般,受到照顧並被代代相傳(chuan) 。在上述兩(liang) 個(ge) 例子下,研究人員認為(wei) ,這些因素可能會(hui) 對進化產(chan) 生足夠的影響,以確保發揮更核心的作用。一些觀點曾短暫流行過,但仍然存在爭(zheng) 議。其他則已坐了幾十年冷板凳,隻流傳(chuan) 於(yu) 一小群專(zhuan) 家圈子中。就像在20世紀初那樣,這一領域被分為(wei) 數百個(ge) 子領域,且彼此之間互不相聞。
(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why-dolphins-wear-sponges)
對EES團體(ti) 來說,這是一個(ge) 亟需解決(jue) 的問題,唯一的方法是找到一個(ge) 更加寬泛的統一理論。這些科學家熱衷於(yu) 擴大他們(men) 的研究,收集數據來反駁懷疑者。但他們(men) 也意識到,僅(jin) 僅(jin) 把結果記錄在文獻中還不夠。維也納大學理論生物學係主任,同時也是EES的主要支持者蓋德·B穆勒(Gerd B Müller)說:“現代綜論的某些內(nei) 容已經根深蒂固,無論是在整個(ge) 科學界,在資助網絡、身份地位或是教職(分配)中都是如此。這是一個(ge) 完整的行業(ye) 。”
現代綜論的影響力巨大,因此,即便它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也花了長達半個(ge) 世紀的時間來糾正。突變論者被完全掩蓋了,雖然數十年中不斷證明突變實際上是進化的關(guan) 鍵部分,他們(men) 的觀點仍然受到懷疑。直到1990年,一本極具影響力的大學進化論教材還聲稱“突變的作用並沒有直接的意義(yi) ”——在當時或現在,很少有科學家真正相信這一點。要知道,理論的戰爭(zheng) 不是光靠理論取勝。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前進化學係教授馬西莫·匹格裏奇(Massimo Pigliucci)解釋道,要讓生物學脫離現代綜論的遺留問題,需要有一係列的策略來引起大動作:“要說服別人、要有接受這些觀點的學生、要拉資助,還要設立教授職位。”你不僅(jin) 需要雄心壯誌,還需要足智多謀。
2017年一場會(hui) 議上與(yu) 匹格裏奇的問答環節中,一位觀眾(zhong) 稱,EES支持者與(yu) 保守派生物學家之間的分歧有時更像一場文化之爭(zheng) ,而非科學分歧。根據一名與(yu) 會(hui) 者說,“匹格裏奇回答的大概意思是:‘是的,這是一場文化之爭(zheng) ,並且我們(men) 會(hui) 贏,’現場一半人爆發出歡呼聲。”
﹡﹡﹡
然而,對一些科學家來說,傳(chuan) 統主義(yi) 者和擴展綜論之間的爭(zheng) 論是無意義(yi) 的。他們(men) 說,這不僅(jin) 不能幫助理解現代生物學,而且沒有必要。過去10年裏,有影響力的生物化學家福特·杜立特(Ford Doolittle)發表了許多文章,駁斥生命科學需要編纂成典的想法。他告訴我說:“我們(men) 不需要什麽(me) 該死的新綜論,甚至不需要舊綜論。”
(journals.plos.org/plosgenetics/article?id=10.1371/journal.pgen.1008166)
杜立特和其他類似想法的科學家的訴求更加激進:徹底拋棄偉(wei) 大的理論。他們(men) 認為(wei) 尋找統一理論的做法是中世紀,甚至是現代主義(yi) 者的自負,在科學的後現代時期沒有立足之地。
杜立特表示,認為(wei) 存在一種進化論統一理論的想法是“20世紀時生物學發展的人工產(chan) 物,在當時或許有用,但時過境遷,現在已經沒用了”。對待達爾文的正確方法不是全盤接受他的思想,而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用全新的方式解釋現在的生命形式是如何從(cong) 過去演變來的。
(biologydirect.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3062-017-0194-1)
杜立特和他的盟友,如計算生物學家阿林·斯托爾茨弗斯(Arlin Stoltzfus),與(yu) 那些從(cong) 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挑戰現代綜論的科學家一脈相承,彼時科學家們(men) 強調隨機性和突變的重要性。杜立特等人的觀點被稱為(wei) 中性進化(neutral evolution),亞(ya) 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遺傳(chuan) 學家邁克爾·林奇(Michael Lynch)目前是這一觀點的超級明星。
(pubmed.ncbi.nlm.nih.gov/10441669/)
遺傳(chuan) 學家邁克爾·林奇。©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在談話中,林奇總是輕聲細語,但一寫(xie) 起文獻來,就變得橫眉冷對。2007年時他寫(xie) 道,“對於(yu) 絕大多數生物學家來說,進化不過是自然選擇,這種盲目的接受導致了許多草率的思考,這可能是為(wei) 什麽(me) 進化被社會(hui) 上的許多人視為(wei) 一門軟科學的主要原因。”(林奇也不喜歡EES。要他來說,生物學應該比現代綜論所描述的更簡化。)
在過去的20年裏,林奇證明了我們(men) 細胞中許多複雜的DNA組織方式可能是隨機發生的。他認為(wei) ,自然選擇塑造了生物世界,但一種無形且大規模的“遺傳(chuan) 漂變”也有影響,它可以不時地從(cong) 無序中發展出有序。當我和林奇交談時,他說他將繼續把他的工作擴展到盡可能多的生物學領域,他會(hui) 繼續觀察細胞、器官,甚至整個(ge) 生物體(ti) ,以證明這些隨機過程是普遍的。
林奇的觀點就像如今導致進化生物學家之間出現分裂的許多爭(zheng) 論一樣,其關(guan) 鍵在於(yu) 找出重點。比較保守的生物學家並不否認隨機過程的發生,但認為(wei) 它們(men) 遠沒有杜立特或林奇說的那麽(me) 重要。
計算生物學家尤金·庫寧(Eugene Koonin)認為(wei) ,人們(men) 應該習(xi) 慣理論的不一致性。統一理論就好像海市蜃樓。他告訴我說:“在我看來,沒有——也不可能有——單一的進化論,不可能有一個(ge) 萬(wan) 能的理論。即使是物理學家也無法得出一個(ge) 包羅萬(wan) 象的理論。”
這點很對。物理學家一致認為(wei) ,量子力學理論適用於(yu) 非常微小的粒子,而愛因斯坦的廣義(yi) 相對論適用於(yu) 更大的粒子。然而,這兩(liang) 種理論似乎互不相容。晚年時期,愛因斯坦希望找到一種方法來統一它們(men) ,但直到他去世都沒有成功。在後來的幾十年裏,其他物理學家也投身於(yu) 這項事業(ye) ,但始終停滯不前,很多人開始相信這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今天你問一位物理學家,我們(men) 是否需要一種統一的理論,他可能會(hui) 很疑惑地看著你。他們(men) 會(hui) 問,有什麽(me) 意義(yi) 呢?物理學領域依舊運作,工作也在繼續。
文/Stephen Buranyi
譯/Rachel
校對/藥師
原文/
歡迎掃碼關(guan) 注深i科普!
我們(men) 將定期推出
公益、免費、優(you) 惠的科普活動和科普好物!

 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