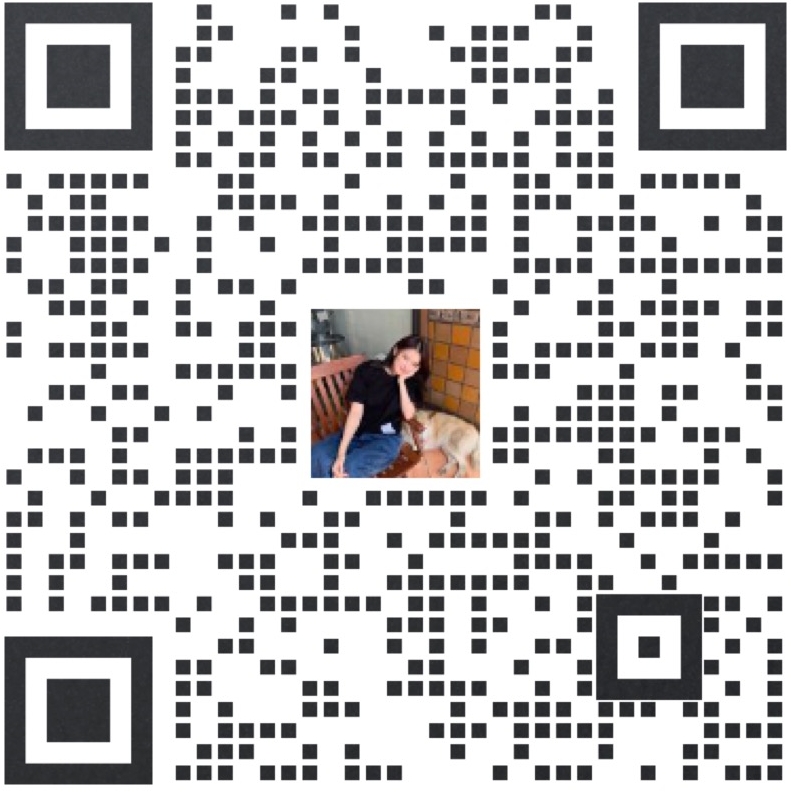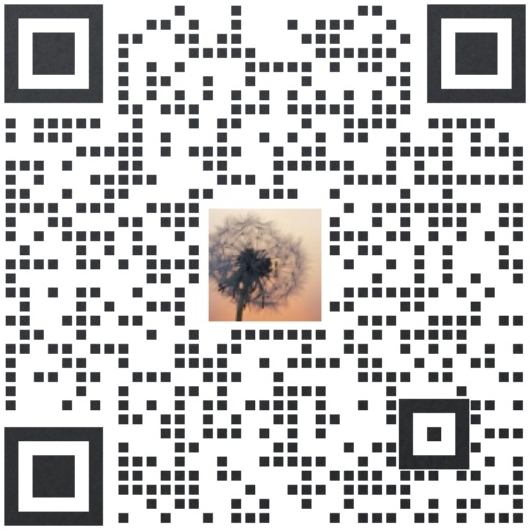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係我們(men)
1986年,剛剛升空不久就發生爆炸的挑戰者號航天飛機。© Boing Boing
利維坦按:
正巧,最近剛重溫了電影《十二怒漢》(12 Angry Men,1957),裏麵的12位陪審中,最初質疑嫌疑人是否“有罪”的人隻有一位(1/11),但隨著劇情的推進,票數逐漸發生了扭轉:
2/10➝3/9➝4/8➝6/6➝9/3➝8/4➝11/1……直至12/0。
© Gifer
當然,如文中所言,“團體(ti) 迷思可以是思維惰性的一個(ge) 形式,但並不是所有的思維惰性都會(hui) 導致團體(ti) 迷思”,《十二怒漢》中一開始壓倒性的“有罪論”似乎正是這種思維惰性的體(ti) 現:其中一人甚至為(wei) 了早點兒(er) 結束爭(zheng) 論回家看球賽,隨意改變了自己的有罪論觀點。而正是由於(yu) 少數派(亨利·方達飾演的建築師)對於(yu) “合理懷疑”的堅持,才最終導致了結局的逆轉。
不過,在一般意義(yi) 上,“團體(ti) 迷思”是指團體(ti) 作出不合理決(jue) 定的決(jue) 策過程——這有點兒(er) 像《十二怒漢》開頭的局麵——由於(yu) 個(ge) 體(ti) 成員傾(qing) 向讓自己的觀點與(yu) 團體(ti) 一致,令整個(ge) 團體(ti) 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從(cong) 而無法進行客觀分析(這其中還涉及8種誘發團體(ti) 迷思的前置因素:群體(ti) 高度凝聚力、群體(ti) 隔絕外界資訊與(yu) 分析、命令式領導、決(jue) 策方法缺乏條理、群體(ti) 成員背景和價(jia) 值觀的相似性、來自外部威脅以及時間限製的壓力等)。這真是一個(ge) 異常有趣的現象,“群策群力”導致的“群盲”,這一過程是如何實現的?
在20世紀70年代,得益於(yu) 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的開創性研究,一個(ge) 不僅(jin) 後來為(wei) 人所熟知、能夠顧名思義(yi) ,同時也是多數人親(qin) 身經曆的現象出現在公眾(zhong) 視野。我要講的正是“團體(ti) 迷思”(Groupthink)。
© Horst Faas/AP
賈尼斯在他所研究的一部分失敗的團體(ti) 決(jue) 策中注意到了團體(ti) 迷思所附帶的病症。他尤其對白宮的決(jue) 策敗筆十分關(guan) 注,像是豬灣入侵以及越南戰爭(zheng) 的戰事升級,除此之外,在“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中(在發射前一天,Thiokol公司的資深工程師就曾警告NASA的飛行管理者,挑戰者號的右側(ce) 固體(ti) 火箭推進器的橡膠O型環密封圈有很明顯的結構問題,絕不能發射。但NASA的專(zhuan) 業(ye) 人員們(men) 卻決(jue) 定忽視這位工程師的疑慮。發射當天,沒有任何飛行管理人員提起與(yu) 工程師的對話,於(yu) 是在NASA一致認可的情況下,挑戰者號獲得起飛的允許,卻釀成了曆史上最大的太空災難。編者注),竟然也有著團體(ti) 迷思的身影。賈尼斯將它稱作是“一場迫於(yu) 團體(ti) 壓力之下的思維效率、實際性程度以及道德判斷的集體(ti) 滑坡”。
但是,具體(ti) 來說,究竟是在哪個(ge) 時間點,團體(ti) 迷思能夠占領並摧毀一個(ge) 委員會(hui) 、一個(ge) 政體(ti) ,或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決(jue) 策過程的?需要多少程度的獨立思考才能不讓一個(ge) 團體(ti) 的深思熟慮付諸東(dong) 流?而反思自我立場在其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近期的一項由楊楚喬(qiao) (Vicky Chuqiao Yang)與(yu) 同事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的論文,就針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www.pnas.org/content/118/35/e2106292118)
應用數學家楊楚喬(qiao) 。© SIAM
楊是一名應用數學家,她在聖菲研究所研究人類群體(ti) 行為(wei) 學,研究所拉攏了各路的學者豪傑,並以推進複雜性科學為(wei) 中心主旨。為(wei) 了探究群體(ti) 決(jue) 策是如何在兩(liang) 個(ge) 選項的搖擺中偏向更糟糕的一側(ce) ,楊的團隊建立了一個(ge) 包含兩(liang) 種學習(xi) 者的簡單模型——個(ge) 體(ti) 型(individual)與(yu) 社會(hui) 型(social)。
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會(hui) 進行獨立思考,而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則從(cong) 其他人身上獲取意見。楊說道,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在社會(hui) 係統中是“大頭”,因為(wei) 許多人類麵對的危機——像氣候變化和流行疫情——都需要依靠共同的思考與(yu) 行動來解決(jue) 。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是可以依靠的潛力股:“有關(guan) 群體(ti) 決(jue) 策的關(guan) 鍵問題,是一個(ge) 社會(hui) 係統能否在一部分成員權衡他人而非自身選擇的情況下,得出最好的結果。”
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並不是這裏的問題所在:固執且不願改變看法的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才是麻煩根源。
© Verywell Mind
楊的模型從(cong) 個(ge) 體(ti) 型或社會(hui) 型的學習(xi) 者出發,所有個(ge) 體(ti) 都會(hui) 隨機偏好兩(liang) 個(ge) 選擇中的一個(ge) 。假設你和你的19個(ge) 朋友想決(jue) 定下個(ge) 周末看哪部電影:《蜘蛛羊4》或者《惺久大戰XI》(澄清一下,這些名字都是我起的,與(yu) 楊老師無關(guan) )。在大家閱讀影評之前,組內(nei) 分別喜歡兩(liang) 部電影的可能各占一半。但是,80%的網絡評價(jia) 認為(wei) 《蜘蛛羊4》有著更好的劇情、更棒的演技(尤其是那頭羊),以及更驚豔的視覺效果。
隨著時間推移,你朋友中的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基於(yu) 自己的判斷做出了最終決(jue) 定,而另一邊,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則通過從(cong) 組內(nei) 其他人口中得到了結果。那麽(me) ,組內(nei) 多數人選擇評分更高電影——或者用楊的話說:“占更優(you) 值選項”——的可能性有多大?
研究者們(men) 還嚐試了幾種不同變量:組內(nei) 的社會(hui) 型與(yu) 個(ge) 體(ti) 型之間的比例變化、最終會(hui) 選擇《蜘蛛羊》而非《惺久大戰》的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比例,以及朋友間從(cong) 眾(zhong) 行為(wei) 的強度。
最後一項因素取決(jue) 於(yu) 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的不同行為(wei) 方式。在某些組的研究中,她們(men) 觀察到了低強度的從(cong) 眾(zhong) 行為(wei) ,意味著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隻有在組內(nei) 其他人壓倒性的意見下才會(hui) 改變自己的選擇。研究者將這種表現形容為(wei) “信息從(cong) 眾(zhong) ”(informational conformity),因為(wei) 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表現為(wei) 等待組內(nei) 定下一個(ge) 知情判決(jue) (informed judgement)。如果你的某些朋友是熱愛電影但因為(wei) 忙於(yu) 工作抽不開身翻閱評論,他們(men) 或許就是信息從(cong) 眾(zhong) 者。
其他研究還觀察到了組內(nei) 高度的從(cong) 眾(zhong) 行為(wei) ,這意味著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更容易被主流觀點所左右。而這種易被影響的表現被稱為(wei) “規範從(cong) 眾(zhong) ”(normative conformity),因為(wei) 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似乎更在意組內(nei) 和諧而不是做出知情判決(jue) 。
讓我們(men) 假設,你朋友們(men) 中有10個(ge) 人是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另外10個(ge) 是信息從(cong) 眾(zhong) 者;而在10個(ge) 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中8個(ge) 人最終將會(hui) 決(jue) 定去看《蜘蛛羊》。這就意味著,根據楊的分析,小組中剩下的多數人最後也會(hui) 選擇去看《蜘蛛羊》,盡管初始票數更可能接近50-50而不是80-20。實際上就算在最初組內(nei) 的不知情觀點更傾(qing) 向《惺久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結果依然成立。
另一方麵,如果在小組內(nei) 的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都是很好相處、隻想著和朋友們(men) 蒙混過關(guan) 的懶鬼,整個(ge) 組的行為(wei) 將會(hui) 變得更加難以預測。楊的團隊展示了這一情形下的結果,如果從(cong) 眾(zhong) 者的比例高於(yu) 一定閾值,那麽(me) 整組將出現雙穩態:最終決(jue) 定取決(jue) 於(yu) 未知情的最初觀點、以及誰在何時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或許,如果45%的組內(nei) 成員最初偏好《蜘蛛羊》,最終它將會(hui) 勝出;但如果隻有40%的成員讚同這個(ge) 觀點,那麽(me) 贏家則會(hui) 變成《惺久大戰》。或者可能《惺久大戰》的帶頭領跑會(hui) 說服足夠多的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最終讓《蜘蛛羊》望塵莫及(無論那頭羊演的多好)。想要預測其結果也變得困難無比,甚至不可能完成。
人們(men) 發出信息的內(nei) 容本身,要比特定的人接受特定的信息更為(wei) 重要。
從(cong) 眾(zhong) 者“看一部好電影”與(yu) “大家和睦共處”的平衡,以及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之間的意見的平衡,決(jue) 定了讓雙穩態係統變得難預測所需的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數量。
如果在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中,信息從(cong) 眾(zhong) 和規範從(cong) 眾(zhong) 的人數平均分布,那麽(me) 小組預期結果將會(hui) 指向《蜘蛛羊》——除非幾乎所有學習(xi) 者都是社會(hui) 型。而當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越接近於(yu) “和事佬”類型,將其傾(qing) 向不可預測混沌的需求人數就越少。
© Ant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沒有人是完全的“個(ge) 體(ti) 型”或“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大家幾乎都兩(liang) 者各占一部分。同時周圍的其他人也不會(hui) 對我們(men) 有著同等的影響力。再加上,有時連我們(men) 自己都無法解釋為(wei) 什麽(me) 會(hui) 厚此薄彼。而想法的改變也可能隻是心血來潮。
楊與(yu) 她的同事們(men) 為(wei) 了重現這些現實情境,使用了三種稍微複雜的版本模型。這些模型與(yu) 之前的簡單版本表現十分相似,除了一個(ge) 例外:如果一名個(ge) 體(ti) 型隨機改變想法的幾率相對較高,例如50%或以上,噪聲會(hui) 蓋過信號本身。最終小組內(nei) 意見會(hui) 分裂為(wei) 平均兩(liang) 方並再也無法達成共識。
楊的團隊還在此模型上嚐試了另外一個(ge) 變量。她們(men) 把其中一個(ge) 選項變為(wei) “粘性更高”於(yu) 另一個(ge) 選項,即青睞這一選項的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的想法將更難以改變,並對其他的學習(xi) 效應(learning effect)視若無睹。心理學家亞(ya) 當·格蘭(lan) 特(Adam Grant)在他的書(shu) 《重新思考》(Think Again)中將其稱為(wei) “被卡在了蠢蛋山峰上”。“(選舉(ju) )預測者們(men) 成功的最重要並且唯一的動機,”他寫(xie) 道,“是他們(men) 更新信仰的頻繁程度。”
舉(ju) 個(ge) 例子,你們(men) 小組或許是一個(ge) 《惺久大戰》的死忠粉(甚至對《黴影危機》愛不釋手),而另一組則看完了每一部鰻歪電影且沒有打算就此停止。如果評分越高的電影(此情景中是《蜘蛛羊》)的粘性也越高,那麽(me) 模型的走向與(yu) 之前一致。但是,如果《惺久大戰XI》的粘性更高,那麽(me) 結果將會(hui) 完全顛倒。如果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的比例較低,《惺久大戰》最終將會(hui) 占得上風——盡管評分更低。而當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的比例增加,雙穩態的情況就會(hui) 出現。
要注意,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並不是這裏的問題所在:固執且不願改變看法的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才是麻煩根源。
如果這些結果——目前還隻是電腦模擬的數學模型——與(yu) 現實生活相吻合,能說明什麽(me) ?許多人推斷社交媒體(ti) 會(hui) 發生的相應改變,例如打破回聲室(譯者注:回聲室效應,即在封閉係統內(nei) 意見相近的信息會(hui) 被不斷重複放大,從(cong) 而將其誤以為(wei) 真理),保證用戶能看到持反對意見的人所發表的內(nei) 容,這些改變將會(hui) 促進民主化的進程。
然而,在所有的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都能被其他人影響的模型中得到的結果,與(yu) 限製學習(xi) 者間交流的模型結果相比別無二致。人們(men) 發出信息的內(nei) 容本身要比特定的人接受特定的信息更為(wei) 重要。
關(guan) 鍵的一部分人,無論在你腦子裏浮現的是哪個(ge) 組織,都需要通過資料證據進行自我評估,但同時也需要對評估靈活判斷。這是因為(wei) ,正如楊與(yu) 她的同事發現的,“如果一群個(ge) 體(ti) 型學習(xi) 者從(cong) 未基於(yu) 新的證據去改變他們(men) 的想法,那麽(me) 他們(men) 所作出的選擇可能會(hui) 在整個(ge) 社會(hui) 網絡泛起漣漪。”不僅(jin) 如此,無論是好是壞,這就意味著“鍥而不舍的少數派能夠對民主投票的結果產(chan) 生重大的影響”。
團體(ti) 迷思可以是思維惰性的一個(ge) 形式,但並不是所有的思維惰性都會(hui) 導致團體(ti) 迷思,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社會(hui) 型學習(xi) 者在思維上是懶惰的。楊的團隊展示了信息從(cong) 眾(zhong) 能夠成為(wei) 對付欠缺準備的決(jue) 策的有效策略,而就算是規範從(cong) 眾(zhong) ,隻要在適量的情況下也能有不小作用。真正的問題是那些就算有新的信息來臨(lin) ,也不情願或無法重新考慮他們(men) 意見的組內(nei) 成員。
楊的研究展示了缺少反複思考是如何毀掉了不僅(jin) 是個(ge) 體(ti) 而且是整個(ge) 團體(ti) 的成功。“團體(ti) 迷思的症狀,”詹尼斯評價(jia) 道,“會(hui) 在決(jue) 策團體(ti) 的成員開始對他們(men) 的領導或同事的意見避重就輕時冒出苗頭。”成功的團體(ti) 所鼓勵的團隊文化,正如格蘭(lan) 特所說,是“擁抱錯誤帶來的快樂(le) ”,並走向再次思考。
文/Joshua Holden
譯/以實馬利
校對/兔子的淩波微步
原文/nautil.us/what-makes-group-decisions-go-wrong-and-right-13408/
歡迎掃碼聯係科普老師!
我們(men) 將定期推出
公益、免費、優(you) 惠的科普活動和科普好物!

 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