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那些為CRISPR做出貢獻的年輕研究者,也應被銘記
科學研究:那些為CRISPR做出貢獻的年輕研究者,也應被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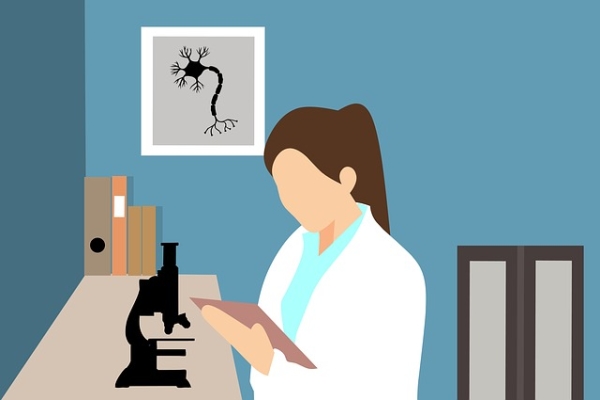
圖片來源:Vasava|Nature
當Blake Wiedenheft開始微生物學研究時,他的工作相當冷門、前途未卜。
他博士期間的主要工作是在黃石國家公園的溫泉中采樣,然後在實驗室中再現這一生態係統,以此來研究這些在惡劣水環境中生存的微生物。“我們想知道生命是如何在沸騰的酸液中存活的。”他說道。
一段時間之後,Wiedenheft的興趣轉向了微生物的病毒防禦機製。他閱讀了很多相關的研究,無意中看到了一個名為CRISPR的奇特細菌免疫機製。2007年,他聯係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Jennifer Doundna,發現她也有相同的興趣。Doundna隨後邀請Wiedenheft來到她的實驗室工作。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裏,他展開了針對CRISPR係統的結構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研究,以第一作者發表了一篇Nature論文。
今天,對於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學家來說,CRISPR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研究者們急切地想要將這一係統擴展應用於生命王國中的各種基因組,用來插入或切除DNA序列。CRISPR被用於培育新品種的轉基因作物,未來可能會用於治療人類遺傳性疾病。Doudna和其他最早投身相關工作的研究者都成為了科學明星:他們在主流報紙上露麵、在紀錄片中出鏡,而且常有傳言說他們會成為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編者按: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已成為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當我加入實驗室的時候,我是實驗室裏唯一一個研究CRISPR的人,”Wiedenheft說,“而當我離開的時候,實驗室裏幾乎每一個人都在研究它。”
然而,和其他用辛勤工作將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變為現實的研究生和博士後一樣,Wiedenheft沒能像他的導師一樣獲得巨大聲譽。他們當然也從這項工作中獲益:他們收獲了導師的支持、分享著導師的光環,同時也熟練掌握了一項熱門技術。但在試圖轉換身份、以獨立研究者的身份進入這一超級熱門研究領域的過程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感到艱難。
對Wiedenheft來說,生存的關鍵在於急流勇退。離開Doudna的實驗室之後,他放棄進入一家更大更知名的研究機構工作的機會,選擇回到博士生期間的母校蒙大拿州立大學任職。“在一天的工作之後,我可以有獨處和室外活動的機會。這讓我更有創造力,成為更好的科學家。”他說。但是和許多出身於超一流實驗室的年輕科學家一樣,他也時常會想,在生物醫學領域,如果將榮譽歸於第一作者,而非最後的作者,他的生活將會有何不同。他承認,有些時候他會感到沒有得到足夠的賞識。“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很重要,有時候卻又並非如此。”

圖片來源:Vasava|Nature
被修改的CRISPR研究史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發曆史已經成為了一個充滿激烈爭議的話題,並引發了殘酷和高風險的專利戰爭。研究者和研究機構都爭先恐後、互不相讓,一定要確保學術論文和新聞報道中都提及自己的貢獻。“我接到了很多律師的電話,詢問我究竟在什麽時間做了什麽工作。”Wiedenheft說。
2020年1月,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所長EricLander往這一爭論雷區扔下了一篇名為《CRISPR的英雄們》(The heros of CRISPR)的曆史性側寫報道(編者按:該文完整中文版請看今日推送第二條),立即引爆了爭議。有人說文章邊緣化了某些研究者的貢獻,而另一些人表示,博德研究所正置身於一場關於誰是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發明者的專利糾紛之中,而這篇文章中卻沒有相應的利益衝突聲明。
對於同樣是該領域先驅的哈佛醫學院教授George Church來說,讓他感到最不舒服的是,這篇文章將相關的關鍵發現劃歸在他本人,而不是他手下博士後與研究生。“Eric將我的名字提及了太多次。”Church說。
Lander說,他的“英雄”文章並沒有刻意忽視任何人。他清楚知道,關鍵的文章有幾十名共同作者,“但我沒有辦法在一篇9頁的文章中講述他們每個人的故事。”他補充表示,這篇文章實際上擴展了CRISPR的關注焦點:在此之前,大家的關注和討論都集中在領域中3位主要貢獻者身上,而他的文章則刻畫了17個關鍵人物,並且提醒大家還有更多的人參與其中。
盡管導師們強烈呼籲關注年輕的科研人員,他們依然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Church實驗室的年輕人對他給予的堅定支持,以及他提供的獨一無二的學術環境大力讚美。而Doudna也是她所培養的年輕研究者們的堅實領袖。“讓年輕人獲得應得的聲譽十分重要,”她說,“是他們在真正推動科學的進步。”所幸,在學術論文中,每一位作者的具體貢獻通常都會得到記錄。
但是這些細節常常被忽視,隻是因為在當前的環境下,科學聲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獎項通常都歸屬於實驗室的領導者。“這就是體係運作的方式,而我接受我在體係中的角色,”Doundna實驗室的另一名成員Martin Jinek說,“但是沒錯,你還是會情不自禁地想到這些事。”
研究生畢業於Doudna實驗室,如今擔任加州伯克利Caribou Biosesciences公司董事長的Rachel Haurwitz表示,有時候人們會注意到第一作者的名字,但這並沒有意義。她說:“他們會提到‘2012年Jinek那篇文章’,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Martin Jinek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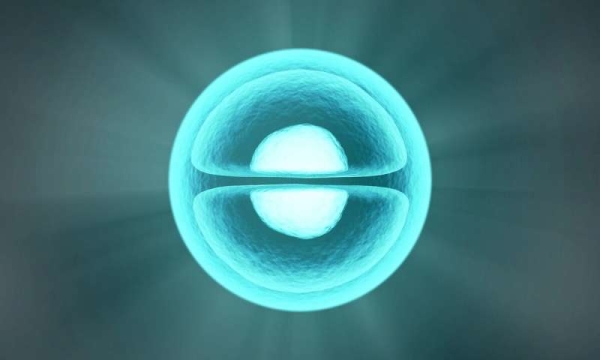
圖片來源:Pixabay
Jinek是一篇開創性文章的共同作者,這篇文章發現,僅僅在一條短鏈RNA的引導之下,Cas9酶就可以靶向作用於特定的DNA序列。那之後他發現,CRISPR定義了他的人生。踏入求職市場的時候,由於專利還沒有完成審批,他甚至不能在麵試中提起相關的工作。即便如此,他還是得到了瑞士蘇黎世大學提供的誘人工作,他開始在那裏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致力於研究CRISPR的基礎生物學問題,而較少涉及應用。
隨著人們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興趣的增長,他的日程也緊湊起來:現在他每個月都要出差兩到三個次作報告。在享受著CRISPR帶來的事業紅利的同時,他也要想方設法在實驗室運營和其他事務中取得平衡。
Haurwitz也同樣麵臨著阻礙。她在博士生期間致力於CRISPR微生物免疫係統的鑒定以及一種名為Cys4的CRISPR相關蛋白的結構研究。2011年,她和Doudna等人共同創立了Caribou,來推進CRISPR相關科研工具的商業化。創業早期十分艱難,但Caribou已經成功地與工業界的重要夥伴建立了合作關係。公司在2016年5月宣布在最新一輪融資中得到3千萬美元。隨著公司的發展,一些投資人提出讓經驗更加豐富的管理者取代Haurwitz的位置。“沒有任何撤換她的理由,”Doudna說,“她一直以來都在證明她擁有取得成功的天賦。”
踏浪而行
對於許多處於事業早期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在一個如此熱門的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有著明顯的優勢。博士後期間,PrashantMali促成了CRISPR相關研究在Church實驗室的開展。他是該實驗室201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這篇文章顯示CRISPR-Cas9可以應用於人工誘導多能幹細胞的基因編輯。
這項發現將針對CRISPR的熱情推向高點。同年晚些時候,Mali就踏著這道熱情的巨浪進入了求職市場。“我確實從這項研究中獲取了很多支持。”他說。(然而就像Church所寒心之處一樣,《CRISPR的英雄們》中並沒有提到他)最終就職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之後,Mali繼續從事幹細胞發育和CRISPR相關技術的研究。同時他也接受著這一研究領域的熱度所帶來的小小代價。他說,他隻有18個月大的實驗室非常年輕,工作不至於被同行搶發,但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很顯然,好的點子總會被不止一個人想到。”
CRISPR也為楊璐菡開啟了新的大門,她是Church實驗室2013年那篇Science文章的另一名第一作者。在文章發表後不久,就有幾名從事器官移植的研究者與實驗室取得了聯係。他們想知道這種基因編輯技術能否應用於豬的器官改造,以減少豬器官在人體內引發的免疫反應。Church說,楊璐菡對於實踐這一想法充滿熱情。
豬的基因組中含有逆轉錄病毒DNA,考慮到這些逆轉錄病毒可能會在人類宿主體內重新激活,許多研究者都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退出了豬器官人體移植的研究領域。楊璐菡認為,由於這些逆轉錄病毒基因序列十分類似,通過單次CRISPR-Cas9實驗有可能同時敲除其中的多個拷貝。她和另外3名共同第一作者以一次實驗同時敲除62段目標序列的成績保持著單次CRISPR-Cas9實驗敲除最多目標序列的世界紀錄。為了和Church共同創立名為eGenesis的公司來推進相關工作,楊璐菡正在籌集資金。她說:“George總是給我機會鍛煉自己的領導能力。”
從Church的實驗室出發跨過查爾斯河,博德研究所的生物工程學家張鋒和他的研究生叢樂一起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著,他們的目標是在哺乳動物細胞中發展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叢樂剛剛加入張鋒實驗室的時候,張鋒還是一個剛剛開始建立自己實驗室的年輕研究者。叢樂還記得他打開了裝有實驗室第一台離心機的箱子,然後和張鋒一同坐在電腦前搜索“DNA結合蛋白”,尋找基因組編輯的新方法。這兩個人就組成了一個緊密而高效的研究團隊。
進入CRISPR研究工作後,叢樂開始了對酶的種類和反應條件的漫長篩選,試圖從中找到能夠應用於人體細胞的工作體係。
叢樂樂於冒險。他和張鋒曾經率先使用另一種名為TALENs的基因編輯係統對哺乳動物細胞進行基因編輯,由於有這項工作,即使CRISPR的課題失敗他依然能夠順利畢業。結果是,他並不需要去實踐這個“即使”:2013年,叢樂和另一名研究生FeiAnnRan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證明CRISPR係統可以被應用於哺乳動物細胞。這篇文章與Mali和Church研究組的工作同時發表。
此時,有人建議叢樂跳過博士後階段直接謀求教職。但是他擔心這樣會限製自己的發展:他會被貼上“CRISPR小子”的標簽。“我不喜歡那樣的感覺,”他說,“我不希望單純做一個技術開發者。”於是,叢樂申請了另一份博士後工作,並在幾年後的現在開始謀求教職,他希望自己未來的實驗室從事過敏反應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的研究。
叢樂說,他並不因為CRISPR相關的新聞報道和關注集中在張鋒身上卻忽略了他而感到不滿。“我已經得到了我應得的認可。”他說。張鋒一直慷慨地在學術界幫他建立聲譽,而且還鼓勵叢樂代替自己進行報告。
但是和這篇報道中的其他受訪者一樣,叢樂也認為應當給予領域內其他研究者更多的認可。他在這裏還提到了其他實驗室的相關工作,包括那些鑒定了CRISPR係統的早期微生物學研究。Wiedenheft表示,這就是CRISPR研究圈子的特點,“充滿競爭性,但是真誠友好。”
然而,在這個圈子之外,各種讚譽依然隻由高級學者享有。“我們需要找到擴大榮譽範圍的方法,”Lander說,“認為一項科學研究隻涉及一個、兩個或者三個研究者的想法隻適用於19世紀。”
除了本文中提到的這些人,還有很多CRISPR的幕後英雄。一個經常被遺漏的研究組是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的Virginijus Siksnys團隊。2007年,Giedrius Gasiunas在這裏開始了他的博士生涯。他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專注於CRISPR-Cas9生化性質的研究,最終和Jinek一樣,得出了Cas9酶可以定點切割DNA的結論。
2012年,這個實驗室向Cell投出了一篇文章,結果沒有進入專家評審階段就被拒稿了。Gasiunas隨後將文章轉投PNAS,在數月的漫長等待之後,這篇文章依舊處於評審階段,而此時,Jinek的文章發表於Science。這兩篇文章內容差別很大,但指向相似的結論。Gasiunas的文章被搶發了。
Gasiunas現在成為了Siksnys實驗室的一名博士後,他有時會因為關於CRISPR的讚譽都落到了其他研究者身上而感到苦惱。但是這一次的經曆還沒有完全打消他對這一領域的興趣。後來他的工作又一次被搶發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不像之前那麽難受了。“這是一個高風險的領域,”他說,“但我認為,如果想要得到出色的成果,就必須接受風險。”
撰文:Heidi Ledford
翻譯:趙維傑
審校:紫蘇
引進來源:Nature
引進鏈接:https://www.nature.com/news/the-unsung-heroes-of-crispr-1.20272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關注【深圳科普】微信公眾號,在對話框:
回複【最新活動】,了解近期科普活動
回複【科普行】,了解最新深圳科普行活動
回複【研學營】,了解最新科普研學營
回複【科普課堂】,了解最新科普課堂
回複【科普書籍】,了解最新科普書籍
回複【團體定製】,了解最新團體定製活動
回複【科普基地】,了解深圳科普基地詳情
回複【觀鳥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學習觀鳥相關科普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
回複【博物學院】,了解更多博物學院活動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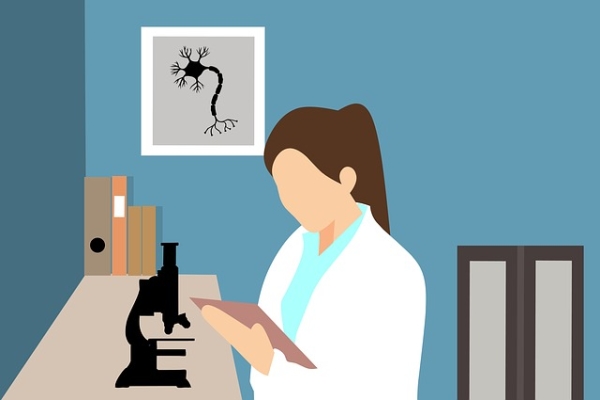
圖片來源:Vasava|Nature
當Blake Wiedenheft開始微生物學研究時,他的工作相當冷門、前途未卜。
他博士期間的主要工作是在黃石國家公園的溫泉中采樣,然後在實驗室中再現這一生態係統,以此來研究這些在惡劣水環境中生存的微生物。“我們想知道生命是如何在沸騰的酸液中存活的。”他說道。
一段時間之後,Wiedenheft的興趣轉向了微生物的病毒防禦機製。他閱讀了很多相關的研究,無意中看到了一個名為CRISPR的奇特細菌免疫機製。2007年,他聯係了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Jennifer Doundna,發現她也有相同的興趣。Doundna隨後邀請Wiedenheft來到她的實驗室工作。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裏,他展開了針對CRISPR係統的結構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研究,以第一作者發表了一篇Nature論文。
今天,對於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學家來說,CRISPR都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研究者們急切地想要將這一係統擴展應用於生命王國中的各種基因組,用來插入或切除DNA序列。CRISPR被用於培育新品種的轉基因作物,未來可能會用於治療人類遺傳性疾病。Doudna和其他最早投身相關工作的研究者都成為了科學明星:他們在主流報紙上露麵、在紀錄片中出鏡,而且常有傳言說他們會成為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編者按: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已成為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當我加入實驗室的時候,我是實驗室裏唯一一個研究CRISPR的人,”Wiedenheft說,“而當我離開的時候,實驗室裏幾乎每一個人都在研究它。”
然而,和其他用辛勤工作將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變為現實的研究生和博士後一樣,Wiedenheft沒能像他的導師一樣獲得巨大聲譽。他們當然也從這項工作中獲益:他們收獲了導師的支持、分享著導師的光環,同時也熟練掌握了一項熱門技術。但在試圖轉換身份、以獨立研究者的身份進入這一超級熱門研究領域的過程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依然感到艱難。
對Wiedenheft來說,生存的關鍵在於急流勇退。離開Doudna的實驗室之後,他放棄進入一家更大更知名的研究機構工作的機會,選擇回到博士生期間的母校蒙大拿州立大學任職。“在一天的工作之後,我可以有獨處和室外活動的機會。這讓我更有創造力,成為更好的科學家。”他說。但是和許多出身於超一流實驗室的年輕科學家一樣,他也時常會想,在生物醫學領域,如果將榮譽歸於第一作者,而非最後的作者,他的生活將會有何不同。他承認,有些時候他會感到沒有得到足夠的賞識。“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很重要,有時候卻又並非如此。”

圖片來源:Vasava|Nature
被修改的CRISPR研究史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發曆史已經成為了一個充滿激烈爭議的話題,並引發了殘酷和高風險的專利戰爭。研究者和研究機構都爭先恐後、互不相讓,一定要確保學術論文和新聞報道中都提及自己的貢獻。“我接到了很多律師的電話,詢問我究竟在什麽時間做了什麽工作。”Wiedenheft說。
2020年1月,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所長EricLander往這一爭論雷區扔下了一篇名為《CRISPR的英雄們》(The heros of CRISPR)的曆史性側寫報道(編者按:該文完整中文版請看今日推送第二條),立即引爆了爭議。有人說文章邊緣化了某些研究者的貢獻,而另一些人表示,博德研究所正置身於一場關於誰是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發明者的專利糾紛之中,而這篇文章中卻沒有相應的利益衝突聲明。
對於同樣是該領域先驅的哈佛醫學院教授George Church來說,讓他感到最不舒服的是,這篇文章將相關的關鍵發現劃歸在他本人,而不是他手下博士後與研究生。“Eric將我的名字提及了太多次。”Church說。
Lander說,他的“英雄”文章並沒有刻意忽視任何人。他清楚知道,關鍵的文章有幾十名共同作者,“但我沒有辦法在一篇9頁的文章中講述他們每個人的故事。”他補充表示,這篇文章實際上擴展了CRISPR的關注焦點:在此之前,大家的關注和討論都集中在領域中3位主要貢獻者身上,而他的文章則刻畫了17個關鍵人物,並且提醒大家還有更多的人參與其中。
盡管導師們強烈呼籲關注年輕的科研人員,他們依然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Church實驗室的年輕人對他給予的堅定支持,以及他提供的獨一無二的學術環境大力讚美。而Doudna也是她所培養的年輕研究者們的堅實領袖。“讓年輕人獲得應得的聲譽十分重要,”她說,“是他們在真正推動科學的進步。”所幸,在學術論文中,每一位作者的具體貢獻通常都會得到記錄。
但是這些細節常常被忽視,隻是因為在當前的環境下,科學聲譽以及隨之而來的獎項通常都歸屬於實驗室的領導者。“這就是體係運作的方式,而我接受我在體係中的角色,”Doundna實驗室的另一名成員Martin Jinek說,“但是沒錯,你還是會情不自禁地想到這些事。”
研究生畢業於Doudna實驗室,如今擔任加州伯克利Caribou Biosesciences公司董事長的Rachel Haurwitz表示,有時候人們會注意到第一作者的名字,但這並沒有意義。她說:“他們會提到‘2012年Jinek那篇文章’,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Martin Jinek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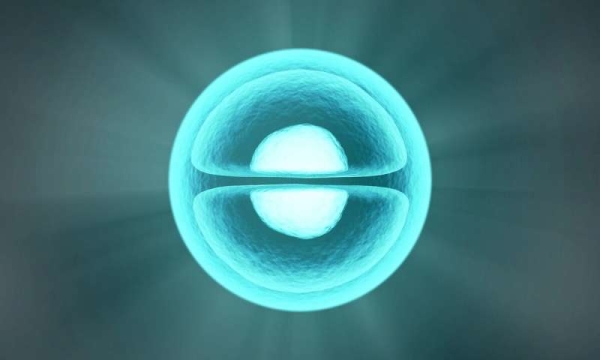
圖片來源:Pixabay
Jinek是一篇開創性文章的共同作者,這篇文章發現,僅僅在一條短鏈RNA的引導之下,Cas9酶就可以靶向作用於特定的DNA序列。那之後他發現,CRISPR定義了他的人生。踏入求職市場的時候,由於專利還沒有完成審批,他甚至不能在麵試中提起相關的工作。即便如此,他還是得到了瑞士蘇黎世大學提供的誘人工作,他開始在那裏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致力於研究CRISPR的基礎生物學問題,而較少涉及應用。
隨著人們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興趣的增長,他的日程也緊湊起來:現在他每個月都要出差兩到三個次作報告。在享受著CRISPR帶來的事業紅利的同時,他也要想方設法在實驗室運營和其他事務中取得平衡。
Haurwitz也同樣麵臨著阻礙。她在博士生期間致力於CRISPR微生物免疫係統的鑒定以及一種名為Cys4的CRISPR相關蛋白的結構研究。2011年,她和Doudna等人共同創立了Caribou,來推進CRISPR相關科研工具的商業化。創業早期十分艱難,但Caribou已經成功地與工業界的重要夥伴建立了合作關係。公司在2016年5月宣布在最新一輪融資中得到3千萬美元。隨著公司的發展,一些投資人提出讓經驗更加豐富的管理者取代Haurwitz的位置。“沒有任何撤換她的理由,”Doudna說,“她一直以來都在證明她擁有取得成功的天賦。”
踏浪而行
對於許多處於事業早期的科學工作者來說,在一個如此熱門的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有著明顯的優勢。博士後期間,PrashantMali促成了CRISPR相關研究在Church實驗室的開展。他是該實驗室201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這篇文章顯示CRISPR-Cas9可以應用於人工誘導多能幹細胞的基因編輯。
這項發現將針對CRISPR的熱情推向高點。同年晚些時候,Mali就踏著這道熱情的巨浪進入了求職市場。“我確實從這項研究中獲取了很多支持。”他說。(然而就像Church所寒心之處一樣,《CRISPR的英雄們》中並沒有提到他)最終就職於加利福尼亞大學之後,Mali繼續從事幹細胞發育和CRISPR相關技術的研究。同時他也接受著這一研究領域的熱度所帶來的小小代價。他說,他隻有18個月大的實驗室非常年輕,工作不至於被同行搶發,但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很顯然,好的點子總會被不止一個人想到。”
CRISPR也為楊璐菡開啟了新的大門,她是Church實驗室2013年那篇Science文章的另一名第一作者。在文章發表後不久,就有幾名從事器官移植的研究者與實驗室取得了聯係。他們想知道這種基因編輯技術能否應用於豬的器官改造,以減少豬器官在人體內引發的免疫反應。Church說,楊璐菡對於實踐這一想法充滿熱情。
豬的基因組中含有逆轉錄病毒DNA,考慮到這些逆轉錄病毒可能會在人類宿主體內重新激活,許多研究者都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退出了豬器官人體移植的研究領域。楊璐菡認為,由於這些逆轉錄病毒基因序列十分類似,通過單次CRISPR-Cas9實驗有可能同時敲除其中的多個拷貝。她和另外3名共同第一作者以一次實驗同時敲除62段目標序列的成績保持著單次CRISPR-Cas9實驗敲除最多目標序列的世界紀錄。為了和Church共同創立名為eGenesis的公司來推進相關工作,楊璐菡正在籌集資金。她說:“George總是給我機會鍛煉自己的領導能力。”
從Church的實驗室出發跨過查爾斯河,博德研究所的生物工程學家張鋒和他的研究生叢樂一起夜以繼日地辛勤工作著,他們的目標是在哺乳動物細胞中發展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叢樂剛剛加入張鋒實驗室的時候,張鋒還是一個剛剛開始建立自己實驗室的年輕研究者。叢樂還記得他打開了裝有實驗室第一台離心機的箱子,然後和張鋒一同坐在電腦前搜索“DNA結合蛋白”,尋找基因組編輯的新方法。這兩個人就組成了一個緊密而高效的研究團隊。
進入CRISPR研究工作後,叢樂開始了對酶的種類和反應條件的漫長篩選,試圖從中找到能夠應用於人體細胞的工作體係。
叢樂樂於冒險。他和張鋒曾經率先使用另一種名為TALENs的基因編輯係統對哺乳動物細胞進行基因編輯,由於有這項工作,即使CRISPR的課題失敗他依然能夠順利畢業。結果是,他並不需要去實踐這個“即使”:2013年,叢樂和另一名研究生FeiAnnRan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證明CRISPR係統可以被應用於哺乳動物細胞。這篇文章與Mali和Church研究組的工作同時發表。
此時,有人建議叢樂跳過博士後階段直接謀求教職。但是他擔心這樣會限製自己的發展:他會被貼上“CRISPR小子”的標簽。“我不喜歡那樣的感覺,”他說,“我不希望單純做一個技術開發者。”於是,叢樂申請了另一份博士後工作,並在幾年後的現在開始謀求教職,他希望自己未來的實驗室從事過敏反應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相關的研究。
叢樂說,他並不因為CRISPR相關的新聞報道和關注集中在張鋒身上卻忽略了他而感到不滿。“我已經得到了我應得的認可。”他說。張鋒一直慷慨地在學術界幫他建立聲譽,而且還鼓勵叢樂代替自己進行報告。
但是和這篇報道中的其他受訪者一樣,叢樂也認為應當給予領域內其他研究者更多的認可。他在這裏還提到了其他實驗室的相關工作,包括那些鑒定了CRISPR係統的早期微生物學研究。Wiedenheft表示,這就是CRISPR研究圈子的特點,“充滿競爭性,但是真誠友好。”
然而,在這個圈子之外,各種讚譽依然隻由高級學者享有。“我們需要找到擴大榮譽範圍的方法,”Lander說,“認為一項科學研究隻涉及一個、兩個或者三個研究者的想法隻適用於19世紀。”
除了本文中提到的這些人,還有很多CRISPR的幕後英雄。一個經常被遺漏的研究組是立陶宛維爾紐斯大學的Virginijus Siksnys團隊。2007年,Giedrius Gasiunas在這裏開始了他的博士生涯。他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專注於CRISPR-Cas9生化性質的研究,最終和Jinek一樣,得出了Cas9酶可以定點切割DNA的結論。
2012年,這個實驗室向Cell投出了一篇文章,結果沒有進入專家評審階段就被拒稿了。Gasiunas隨後將文章轉投PNAS,在數月的漫長等待之後,這篇文章依舊處於評審階段,而此時,Jinek的文章發表於Science。這兩篇文章內容差別很大,但指向相似的結論。Gasiunas的文章被搶發了。
Gasiunas現在成為了Siksnys實驗室的一名博士後,他有時會因為關於CRISPR的讚譽都落到了其他研究者身上而感到苦惱。但是這一次的經曆還沒有完全打消他對這一領域的興趣。後來他的工作又一次被搶發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已經不像之前那麽難受了。“這是一個高風險的領域,”他說,“但我認為,如果想要得到出色的成果,就必須接受風險。”
撰文:Heidi Ledford
翻譯:趙維傑
審校:紫蘇
引進來源:Nature
引進鏈接:https://www.nature.com/news/the-unsung-heroes-of-crispr-1.20272
本文來自:環球科學
關注【深圳科普】微信公眾號,在對話框:
回複【最新活動】,了解近期科普活動
回複【科普行】,了解最新深圳科普行活動
回複【研學營】,了解最新科普研學營
回複【科普課堂】,了解最新科普課堂
回複【科普書籍】,了解最新科普書籍
回複【團體定製】,了解最新團體定製活動
回複【科普基地】,了解深圳科普基地詳情
回複【觀鳥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學習觀鳥相關科普星空体育官网入口网站
回複【博物學院】,了解更多博物學院活動詳情

做科普,我們是認真的!
掃描關注深i科普公眾號
加入科普活動群

- 參加最新科普活動
- 認識科普小朋友
- 成為科學小記者
 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