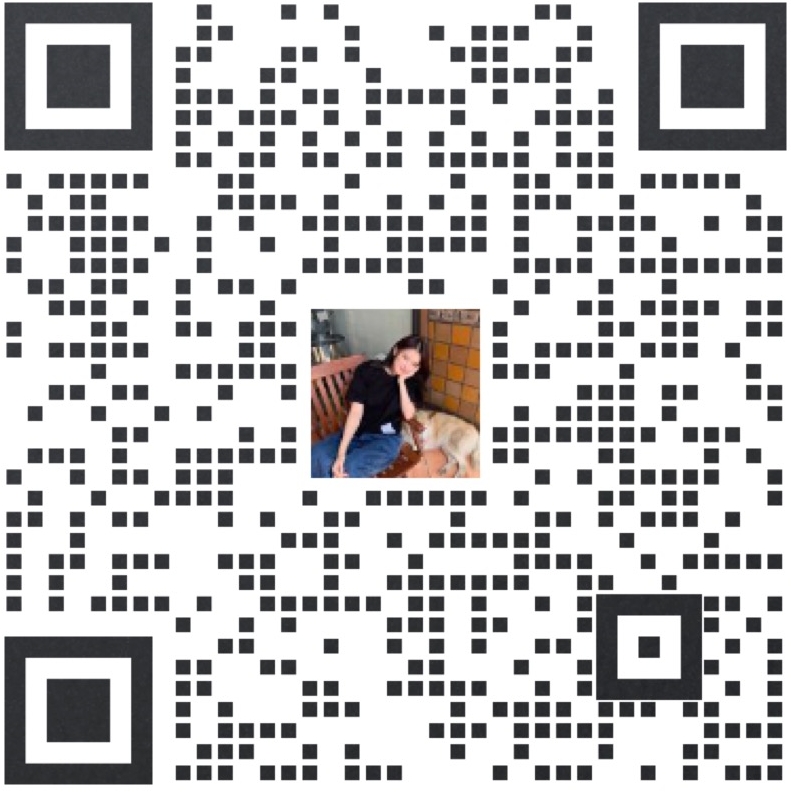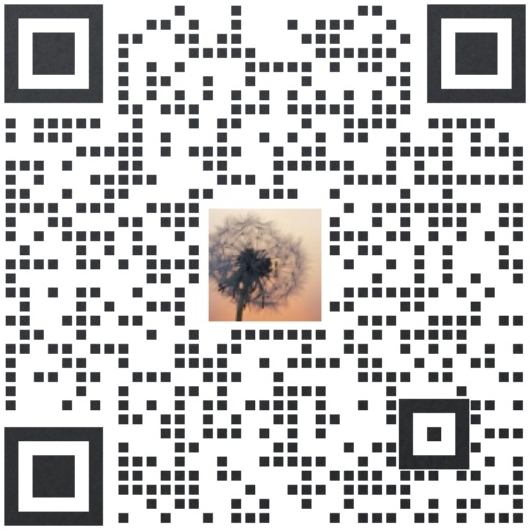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係我們(men)

蔡瀾有一篇文章記述了他的大連之行,特別提到了菜市場裏的燜子。
“小販小火加熱,放進切成小塊的燜子,用筷子翻動把皮煎得焦黃,放入盤中備用。另一廂,用臼子裏搗碎的蒜泥、小磨磨出的麻汁,大量地淋在剛煎好的燜子上麵……就那麽(me) 一吃,哈哈,中了燜子的毒。”
燜子,其實就是地瓜澱粉與(yu) 水混合、攪拌、加熱、凝固成的膠狀的塊,然後再切成小塊,小火少油,慢慢的煎至兩(liang) 麵金黃。
在北方很多地區,這樣熱乎出鍋的燜子,搭配不同的配料,咬下去,軟、糯、香、脆,盡在口中。
01
燜子,大連人的鄉愁
對於(yu) 遠離家鄉(xiang) 的大連人來說,最懷念的味道不會(hui) 是什麽(me) 生猛海鮮,而是燜子。
街邊的一個(ge) 小門臉,支上一大口平底鍋,燜子就在鍋裏滋滋啦啦的作響,一陣小風吹過,沒有大連人能抵抗得了這音效和香氣的雙重誘惑。
製作燜子的原料特別簡便,就是地瓜澱粉和水混合,一邊加熱,一邊攪打成半透明的糊狀,所有做燜子也被叫做“打燜子”。
打燜子一般用地瓜澱粉,也就是紅薯澱粉。與(yu) 其他種類的澱粉相比,地瓜澱粉是所有澱粉裏顏值最低的一種——黑,但是勁力卻特別強,所以燜子才能夠在鍋中久煎不爛。
紅薯澱粉
雖然大連人至愛燜子,但是它的起源並不在大連,而是在渤海對岸的山東(dong) 煙台。
據山東(dong) 福山烹飪協會(hui) 編撰《魯菜之鄉(xiang) ——福山》中記載,燜子是山東(dong) 煙台芝罘島的門氏兄弟不經意中創製出來的。
一百多年前,門氏兄弟在煙台以賣粉條為(wei) 生,有一天粉坯做好了,卻因為(wei) 下雨,做不成粉條。情急之下,門家兄弟請來鄉(xiang) 親(qin) 們(men) ,吃用油鍋煎炒的粉坯。
為(wei) 了防止吃壞肚子,門氏兄弟特意將山東(dong) 特產(chan) 的大蒜搗成蒜醬拌在油煎粉坯中,沒想到這無奈之舉(ju) 居然得到好評。於(yu) 是在大家的建議下,門家兄弟支鍋立灶改做賣油煎粉坯,當食客問及名字時,門家兄弟想了想自己的姓氏,隨口說出“門子”,後來又覺得不妥,取名為(wei) “燜子”。
後來,隨著闖關(guan) 東(dong) 的人潮來到大連,魯菜和各種小吃也接踵而來,其中也包括燜子。
在缺吃少穿的年代,燜子是改善人們(men) 匱乏口味的小吃,隨著物質漸漸充裕起來,燜子成為(wei) 一代大連人的童年記憶。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在大連街頭,經常可以看到商販推著小車或者搭個(ge) 小棚賣燜子。
更常見的其實是在菜市場,大人們(men) 進去買(mai) 菜,孩子們(men) 坐在燜子攤上,用兩(liang) 根細細的鐵絲(si) “窩”成小叉子,紮起一塊煎得焦黃的燜子,小心翼翼地放進嘴裏。
對於(yu) 大連人來說,燜子必須有“ge”。大連話裏的“ge”,其實是煎過之後,最外邊那一層焦脆的外殼,它就像廣東(dong) 煲仔飯裏的鍋巴那樣迷人。
為(wei) 了吃到更多的“ge”,大連的燜子從(cong) 來都不會(hui) 方方正正的,而是各種不規則的形狀,力求增大表麵積。
煎好的燜子外脆裏軟,澆上蒜水和麻醬汁,口水立馬就流下來了。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之後,燜子更是從(cong) 街邊小吃走進了飯館酒樓,搭配海參、蝦仁、螺片做出的三鮮燜子,也成為(wei) 大連菜的代表之一。

02
離開大連,到底還有多少種燜子?
大連人愛燜子,不過燜子也不是大連獨有的。
有一年,在河北秦皇島,一位同學拉著我說,帶你吃一下我們(men) 秦皇島的特產(chan) ——炒燜子。
端上來和大連的燜子一比,不能說很像,簡直就是一毛一樣。
直到去的地方越來越多,才知覺,燜子在整個(ge) 北方是一種普遍的存在。
煙台是燜子的起源地,與(yu) 大連隔海相望,兩(liang) 地的燜子無論是製作、味道還是吃法都差不多。
同樣的地瓜澱粉,同樣的麻醬蒜水,甚至還有同款吃燜子的鐵絲(si) 叉。
唯一稍有不同的是,煙台的燜子還會(hui) 加入蝦油、蝦醬調成的料汁,吃起來海味十足。
其實,很多年前,大連的燜子也有加蝦油的,隻是這些年越來越少見了。
除了大連、煙台、秦皇島,類似的吃法、做法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在丹東(dong) ,燜子會(hui) 切得更方正一些;到了吉林,燜子則改名“煎粉兒(er) ”,雖然名字換了,但東(dong) 西還是那些東(dong) 西。
到了天津,燜子就變得有些不一樣了。
“二月二,龍抬頭。”在天津人的日子裏,二月二除了剪頭發,另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就是吃燜子。
天津的燜子和大連、煙台的不一樣,是用綠豆麵兒(er) 做成的,色澤青碧,又有一些隱約的透明,遠看很像一大塊青玉或者翡翠。
下鍋的時候,切成方方正正麻將塊一般的大小,在平底鍋裏,用一點點油小火煎,煎到幾麵都出現金黃的“嘎兒(er) ”,然後拌入麻醬、鹽、蒜汁兒(er) 和醋,就可以吃了。
綠豆麵兒(er) 做出的燜子,口感更加細膩柔軟。有的天津人家甚至還會(hui) 把燜子、炒合菜一起卷到春餅裏,永恒的碳水配碳水,大餅卷一切。
會(hui) 用綠豆麵兒(er) 做燜子的不隻是天津人,遠在大西北的烏(wu) 魯木齊人,也有用綠豆麵兒(er) 做燜子的習(xi) 慣。
調味料也大差不差,不過淋上新疆的辣椒,燜子味道會(hui) 更香。不同的是,烏(wu) 魯木齊人會(hui) 在農(nong) 曆三月的陽春時節吃燜子。
進入河北,燜子畫風突變,從(cong) 純素的澱粉,到開始有了肉類的存在。
河北定州,當地人把瘦肉絞成小塊(可不能完全絞成肉泥),放到紅薯澱粉糊中一起熬煮、結塊、過涼水、曬幹,最後再經過一道熏製。
這一流程與(yu) 京津地區做“粉腸”的工藝很像。這樣繁瑣工藝做成的定州燜子,就像是一根碩大的香腸,當地人也俗稱“肉灌腸”。
切片後,無論是蒸、炒、燉、拌,都能吃到紮紮實實的肉感。
除了直接加肉,也有借助了肉味兒(er) 的燜子,那就是驢肉火燒裏的燜子。
在驢火屆打得熱火朝天的河間派和保定派,卻能在一件事情上達成共識——燜子。
煮完驢肉的湯和油,絕對不能浪費,把湯燒開,加入澱粉,一邊攪拌,一邊倒入驢油,直到粘稠之後,放冷凝結成凍,就是驢肉火燒中的燜子。
無論是河間派還是保定派,都有在驢肉火燒中加入燜子的做法,對於(yu) 食客來說,一方麵降低成本,另一方麵相比於(yu) 酥脆的火燒和香韌的驢肉,燜子提供了更豐(feng) 富的口感,軟糯與(yu) 酥脆,剛柔並濟。
從(cong) 河北再到河南,禹州的燜子是不加肉的,卻又做出了十足的肉感。
禹州的粉條凍幹煮軟,再加入紅薯粉攪勻,入屜蒸成一大塊。做出來的禹州燜子,煎、炒、烹、炸、燉或是涼拌,甚至可以取代肉的存在。
其實,燜子這種小吃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wei) 物質的不充裕,燜子既能提供與(yu) 肉有那麽(me) 一點點類似的口感,也能有當時並不是太充足的油脂香氣。
類似的物質組合,除了燜子,其實還有陝西的炒涼粉、北京的炸灌腸等等。
時至今日,我們(men) 其實早就擺脫了肉食短缺的窘迫,但對於(yu) 燜子,很多地方卻沒有失去熱情,這當然是因為(wei) ,對於(yu) 脂肪和碳水這個(ge) 黃金組合的熱愛,已經深深地印刻在我們(men) 的基因裏。
同時,焦脆的外殼,軟糯的內(nei) 心,這種外酥裏嫩反差口感,也總是被人追逐。
就算它不再稀缺,也總會(hui) 讓人念念不忘。
END
文 | 衛奕奕
歡迎掃碼聯係科普老師!
深圳科普將定期推出
公益、免費、優(you) 惠的活動和科普好物!



- 參加最新科普活動
- 認識科普小朋友
- 成為科學小記者
 會員登錄
會員登錄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
深圳市龍華區玉翠社區高坳新村小廣場